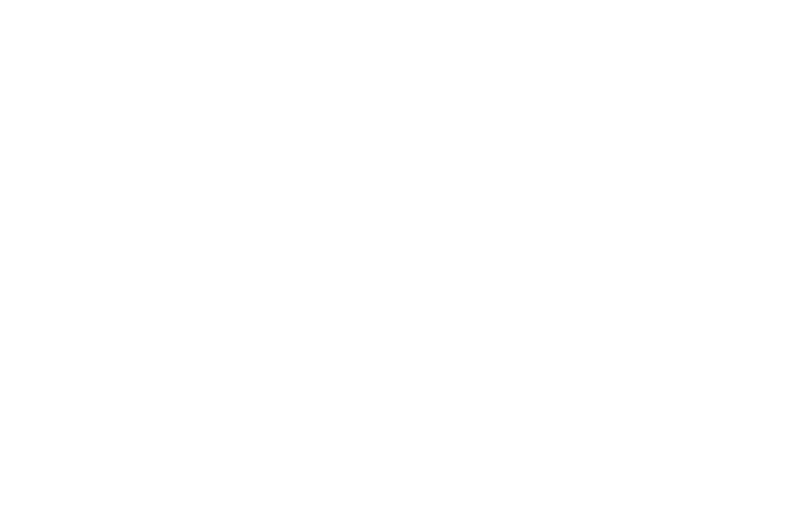文 | 指南者留学·小Z同学
19fall新加坡国立大学园林设计硕士
01
初印象
我与新加坡真正意义上的初见,始源于本科同学的一张简笔的图纸。
现在的我已记不大清那时的情形,只对他展出的一张速写印象深刻。不足A3的草图纸上画着钢结构的树状装置,打印出的照片之中是几棵巨大的、矗立在公园之中的“树”。或许,说是树也不大明确,那是模仿雨树的外形制作出的景观装置Super tree,来自一个我几乎只有模糊概念的国家,一个仿佛与我并无联系的地方,新加坡。
也正是从那一刻开始,这个国家从一个枯燥遥远的名字转化为了更加鲜活的图画,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新加坡于我,开始于耳熟能详的标签:热带国家,华人,花园城市。由于专业影响,即便在从未踏足过那片土地之前我也对它的诸多景点了然于胸,但显然也仅此而已——它依旧是属于海的另一侧的无法抵达的存在。
那时,对于我而言,新加坡似乎也只是地图上的一个色块与一个名字。很大程度上,我们彼此的生活并不会有什么交集,一直等到有一天,我踩在了那块土地之上。
Super tree, Garden by the Bay
02
贯穿始末的酷热
本科毕业旅行的时候去了一趟泰国,对当地深入骨髓的炎热感到后怕。这种恐惧在踏上前往新加坡的飞机后几乎达到了顶峰,我并不敢想象比起泰国更加靠近赤道的新加坡会是如何可怕的天气。
我对热带的印象大约是来自于星际宝贝,穿着草裙、赤着脚在布满椰子树的沙滩上奔跑的小女孩几乎让我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炎热。但出乎意料的是,几乎一年都是夏天的新加坡似乎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炎热。室内大多时间都开着外套也难以抵御的冷气,我还记得洗空调的大叔在结束一次清洗后煞有其事地建议我补充空调的冷凝液,留下我在开足了冷气的房间里瑟瑟发抖。
一半是雨季,一半是旱季,新加坡被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划分为色调迥异的场景,一者是热烈奔放的金灿色,灼热到所见的一切被阳光模糊成蒸笼之中的产物;一者是凉爽阴郁的冷灰色,闪电猝不及防地在天上剌了个口子将雨水一股脑地倒了下来。大多数露天的地方都设置着带顶棚的通道,只是不论是阳光还是暴雨,似乎都会热情地从棚子的边缘摸进来。
遗憾的是新加坡难得有所谓的细雨绵绵,无论起初是多么柔和的雨丝,到最后也大多会演变成震天动地的暴雨。我逐渐习惯了穿着凉拖和轻便的T恤出门,与同样踩着人字拖的邻居大爷一样聚集在食阁买一份海南鸡饭,然后拎着袋子晃悠悠地荡回住所;又或者是在暴雨突来之时下意识地跟人群一起冲进遮雨棚,看着路边成群的鸽子被吓得扑棱着翅膀冲进组屋的楼底。
我好像也在某个瞬间曾经成为新加坡的鸽子。
晴朗的暴雨之中与我一起躲进楼底的鸽子群
03
“Singlish”
作为著名的以华人为主的国家之一,在路上所能见到的华人几乎占了一半。坦白而言,留学的两年除了与学校相关的事务之外,涉及到饮食购物的方方面面我似乎很少用到英语。
在食阁卖东西的大多是说着闽南话或者粤语的叔叔阿嫲,我初来之时也想过用英语点餐,但大多都被他们脱口而出的中文压了回去。楼下附近卖杂菜饭的摊点有个印尼小哥,也早已练就了一嘴比我还要流畅的普通话,与来买饭的阿姨聊得津津有味。但说来惭愧,即便是现在,我也无法说自己能够听明白所有新加坡人的英语,毕竟有时候,当一个可能同时会英语、普通话、闽南语和粤语的人在你面前,他说出的一句话仿佛融合了所有的音调,让我的大脑无法第一时间反应过来那到底是什么。
我最为熟悉的一句话大约是“Can lah(can啦)”,可能是由于我的一位日本老师时常挂在嘴边的缘故,别的诸如“tree(three)”“wah lau(哇咧)”之类的词汇似乎也经常出现,甚至成了习惯。虽然有人调侃Singlish有些难懂,但不得不说语言本身与这个国家的一切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聚集了多个文化的国家才能诞生这样的语言。不管是什么模样的人,换上T恤、裤衩和人字拖,出现在新加坡的街道上,笑眯眯地说着“can lah,can lah”的场景,想想就能让人不约而同地一起笑起来。
班上中国人占了多数,剩下的是几个印度同学,新加坡同学和日本同学。分组作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们一组,于是就有了难得的锻炼口语的机会,甚至偶尔我们会互相教授彼此母语之中的单词,又或者是凑在一起谈论新加坡的文化,调侃彼此的发音,糅杂了英文和中文的新的句子便从中诞生。现在想想,或许一开始新加坡英语的诞生,也是在诸如此类的闲暇交流之中猝不及防、自然而然地出现的吧。
04
海南鸡!海南鸡!
过去的我觉得新加坡应该是热带水果的气味,现在的我觉得新加坡是海南鸡饭的气味。
说起热带,最先想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榴莲,香蕉,芒果,火龙果……但新加坡大大小小的水果摊上,最受欢迎的应该是榴莲,像是小山似的垒成一个又一个带刺的金字塔,除了淡季,只要靠近任何一个摊子,最显眼的气味一定是榴莲。我曾经是个闻到榴莲气味都会跑走的人,现在的我早已经练就了一副在水果摊浓郁的榴莲气味之中面不改色的本领。我的大脑,甚至还能冷静地从我曾经弃之不及的臭味里自动提取出香味,或许这就是人的成长吧。
但是即便在新加坡待的时间改善了我对榴莲的排斥,也没能足够把我转变为它的爱好者,因而我对新加坡饮食的印象自然不会是榴莲,而是海南鸡饭。
你几乎可以在新加坡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它。口味好的店大多藏匿在某个小食阁里,招牌上没有其他菜,排版也仿佛古早港片街头排档一般简单直接。洁白细腻的白鸡和皮棕色红的油鸡一同被挂在橱窗后,老板穿着汗衫手起刀落,动作利索地剖开骨头,将鸡肉片得整齐,码在浸了鸡油的米饭上,从点餐到取餐不会超过三分钟。因此,鸡饭的窗口一般都是食阁里排得最长的,也是最早卖完关门的。或许是因为鸡饭便宜、好吃又迅速,所以青睐它的人很多。
食阁里可供选择的菜色很多,中餐占了多数(大多是福建菜色),也同样有西餐、印度菜和马来菜的窗口,一个食阁一般都会至少配备一个饮料铺,老板拿着冰勺弯腰从冰箱里舀出一大勺冰块丢进杯子,注入柠檬茶或薏米茶,就足够缓解炎热的气候了。
除去食阁之外,自然也有很多各国特色的餐厅,不过因为海南鸡饭陪伴我度过了绝大多数赶论文的时间,因而连回忆都干脆地浸满了好闻的鸡油。无论多难熬的ddl在前,抽空换上拖鞋散步去食阁,买上一份鸡饭慢慢吃完,似乎又重新有了奋斗的动力。
海南鸡饭

05
新加坡的东与西
我在新加坡的两年时间,几乎都待在西海岸附近。
与繁华的东岸不同,西海岸大多都是历史几十年的组屋和condo,少见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办公楼。我所居住的房子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是维护很好,因而无论从内还是外都很难看出它曾在这里存在了那么久。
在这里租屋的大多是学生,学生们的活动范围以NUS为中心朝着周围渗透,生活大多是简单的三点一线,住所—学校—食阁。食阁分布在组屋的各处,挑高的底层被完全空置出来,成为新加坡独有的公共空间。简单而没有丝毫装饰的水泥柱框出的空间之中,我看到过与家乡农村相似的圆桌宴席,看到过花圈簇拥的葬礼,也看到过疲倦的客工就着外套席地而睡的身影。说来很奇妙,人们不同的悲欢离合又或者是已成日常的疲倦,在不同时间聚集在一个同样的空间之中。
而无论前一天这里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吹打唢呐的声响散去,悼念逝者的悲伤散去,家人团聚的喜悦散去,第二天所有的一切都被彻底清空,我站在空无一物的水泥柱之间,感觉曾经参与过这里的一段故事,似乎又没有。
新加坡之西-无意中拍到的天空与组屋的角落
金文泰的地铁串通了我这两年大多数远行的路线。称之为绿线的是最为繁忙的一条,串联了新加坡的东岸与西岸,偶尔在早高峰搭乘地铁的时候,大多难以找到落座的地方,人们行色匆匆地开始自己一天的生活,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们从更为生活化的西侧来到东侧的高楼,进入层叠的写字楼之中,窗外是阳光之中的滨海湾与金沙。
这大约是可以拍下当作壁纸的一幕,只是在游客眼中的风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生活。在东部上班的室友曾说过她看厌了滨海湾的一切,但初来之时,她也和很多人一样曾在那里的角角落落兴奋地留下足迹。
现在想来,新加坡的东岸,这个国家最为繁华的地段,反而是我最为陌生的。由于疫情,这两年我只去过樟宜机场两次,一次是去,一次是回;圣淘沙也好,乌节路也好,滨海湾也好,我在来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去过,离开新加坡的时候去过,无一都只是为了拍照打卡,将这个国家最为出名的地点留存下来,但实际上,那并非我所知道的关于新加坡的生活。
东部的一切象征着我与这里的初识,象征着我与这里的告别,而西部,似乎更像是我曾在这里度过的生活,虽然生活本身或许与组屋之中发生过的宴席一样,第二天就会消失不见,但至少,也切实存在于此。

新加坡所带给我的回忆或许并不仅仅于此,但一时之间,当我们所谈及的事物成为生活,要从习以为常的日常中追溯细节似乎是很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希望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能够有朝一日成为更多人认识过、生活过的地方。
毕竟,它是如此特殊和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