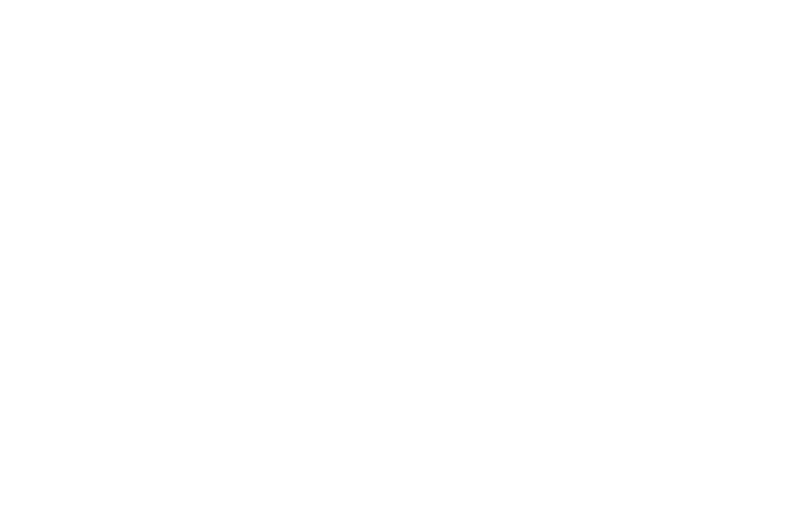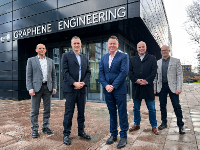这似乎是一对不太可能的组合。其中一位是儿科血液学家莉迪亚·佩克(Lydia Pecker),她在布鲁克林长大,在布朗克斯和华盛顿特区接受训练。另一位是劳伦·安东尼(Lauren Anthony),她从俄克拉荷马州的埃德蒙德(Edmond)招募来,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打排球。但他们因为对镰状细胞病这一种族与医学的复杂交叉领域的共同兴趣而联系在一起。
Pecker为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提供临床护理,并参与了十多年的相关研究,而A&S 22岁的Anthony在休霍金斯研究基金的支持下,在20世纪70年代写了她关于镰状细胞性状测试的高级论文。现在,他们拓宽了他们的关注点。他们正在一起研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镰状细胞研究和治疗的悠久历史。他们的工作是该大学现代学院种族主义和修复项目的一部分,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种族主义、移民和公民计划资助。
“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关于镰状细胞病的很多事情没有改变。这仍然是一种种族化的疾病。这仍然是一种存在巨大医疗差距的疾病。”约翰霍普金斯成人镰状细胞中心青年诊所主任佩克说。
她指出,虽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推进镰状细胞研究和治疗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但传统的财政支持方法,如赠款和慈善事业,远远落后于对其他疾病的资助。
“我们看到的一件事是,关于镰状细胞病的很多事情没有改变。这仍然是一种种族化的疾病。它仍然是一种存在巨大医疗差距的疾病。”
丽迪雅鹤嘴锄
约翰·霍普金斯成人镰状细胞中心青年诊所主任
“关于如何以及是否用资金和临床护理来解决镰状细胞病的决定是几十年前做出的,它们影响着今天的护理和研究。”Pecker说。“如果我们要为镰状细胞病写一个新的故事,我认为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是至关重要的。”
疾病命名
镰状细胞贫血是一种红细胞不再保持圆形和柔软,而是变得弯曲和僵硬的情况。这些细胞堵塞血液,导致缺氧,从而导致剧烈疼痛以及神经和器官损伤。
第一篇关于血液样本显示“镰刀形和月牙形”红细胞的医学论文发表于1910年。但直到1922年,凡尔纳·梅森才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他是医学院1915年的毕业生,当时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住院医师,他将其命名为镰状细胞性贫血。
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但Pecker指出,梅森和他的同行过早地将镰状细胞病确定为一种疾病,因为他们声称这是黑人独有的,这一立场反映了当时医学界(包括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普遍存在的基于种族的思维和意识形态。
“当然,镰状细胞病会影响所有不同肤色的人。”她说。“这是一种遗传疾病,不是种族疾病。”
梅森的文章发表大约20年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名叫欧文·谢尔曼(Irving Sherman)的医学院学生,36年毕业,40年毕业,注意到镰状细胞病患者的红细胞出现双折射。当他发表这一观察结果时,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发现。莱纳斯·鲍林明白其中的意义,十年后,也就是1949年,鲍林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一组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结论是镰状细胞性贫血是一种由蛋白质异常化学结构引起的遗传疾病
尽管如此,直到1972年,国会才通过了《国家镰状细胞贫血控制法案》,授权联邦政府为研究、治疗、咨询、筛查和教育项目提供资金。这项立法无疑提高了镰状细胞病在医学界和公众中的知名度,但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缓解疼痛
这一突破也源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特别是1995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的一项研究,其结果非常有希望,以至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提前停止了一项使用羟基脲治疗镰状细胞性贫血的临床试验。该机构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研究,而是向全球数千名医生发出通知,告知他们羟基脲的有效性。
研究发现,羟基脲可增加镰状细胞病患者胎儿血红蛋白的生成。这可以防止血液中形成镰刀状细胞团块。虽然它不能治愈,但每天服用一次可以显著降低疼痛和组织损伤的频率和严重程度。
这项研究可以追溯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血液学家和医学教授塞缪尔·马歇。characterhe是布鲁克林人,毕业于纽约大学医学院,1966年加入霍普金斯大学,三年后成为医院血液学实验室主任。在20世纪60年代末,charhe开始治疗一个名叫John Paul Jr.的巴尔的摩年轻人,他患有镰状细胞贫血症。
这种疾病让14岁的约翰非常虚弱和痛苦,在他的母亲阻止他之前,他已经准备从桥上跳下去了。他后来说,他不知道疼痛何时开始,也不知道疼痛会在哪里。有时,它来自他的身体深处,有时来自他的眼睛后面。他甚至偶尔在舌头上也能感觉到。
他的母亲薇薇安·保罗(Vivian Paul)不顾一切地寻找一位真正理解儿子所经历的医生,最终找到了查奇,他的绰号“镰刀山姆”(Sickle Sam)不仅反映了他的专业知识,还反映了他对那些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的同情。这是一段28年医患关系的开始。
当trait建议用羟基脲治疗他时,一个信任他且消息灵通的John同意成为第一个为此目的使用羟基脲的镰状细胞病患者。很快,他的弟弟唐纳德·布雷特(Donald Brett)也患有这种疾病,开始服用羟基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药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种痛苦的发作每月一次,可能持续两周。有了羟基脲,约翰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没有出现痛苦的危机。
“在这段历史中。”佩克说,“我们看到的是勇敢的病人,他们被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所困扰。他们很痛苦。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他们的医生,因为他对他们说话的方式,他对他们的关心。”
这是一个让安东尼产生共鸣的故事,因为病人们敢于冒险尝试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也因为约翰·保罗和鲁切在共同开辟一条新路时彼此付出的奉献精神。
安东尼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能成为一名医生。”他计划上医学院。
更大的进步
治疗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另一个突破发生在2012年,当时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血液学部门主任罗伯特·布罗茨基(Robert Brodsky)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表明,即使是部分匹配的骨髓移植,也可以通过用健康的血细胞取代“镰状”血细胞,治愈一些患者的这种疾病。因为任何有兄弟姐妹、父母或孩子的人的基因都是半匹配的,这种手术使得很大比例的骨髓移植患者可以获得骨髓移植。
“我认为大多数人对镰状细胞病的了解程度是,它不成比例地影响非裔美国人,”安东尼说。“但他们不明白它的影响。而且我认为人们不知道这种疗法是最近才出现的。”
对于Pecker和Anthony来说,为镰状细胞病患者提供服务的一个关键方面是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的病情及其身体和情感影响得到清楚的了解和仔细的管理。当他们应对剧烈疼痛发作的唯一选择是冲到急诊室服用阿片类药物时,他们面临着治疗速度变慢和住院时间变长的风险——更不用说被怀疑为获得药物而假装疼痛。
这就是为什么该大学的镰状细胞成人输液中心如此有价值,Pecker说,该中心由Sophie Lanzkron于2008年创立,并已成为全国其他机构的典范。
“我认为大多数人对镰状细胞病的了解程度是,它不成比例地影响非裔美国人。但他们不明白它的影响。而且我认为人们不知道这种疗法是最近才出现的。”
劳伦·安东尼
研究生
“在输液中心,我们的护理团队知道如何正确治疗这些患者。”Pecker说。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性化的护理计划,所以(医疗专业人员)给正确的病人提供正确的药物。
“如果你能想象自己是一个极度痛苦的病人。”她继续说,“然后你必须在一个不可预测和污名化的护理环境中得到护理,就像有时在急诊科遇到的那样。这让情况变得更糟。”
她引用了最近的一项发现,疼痛严重的患者在输液中心接受治疗不到一个小时,而在急诊室需要两个多小时。研究发现,在急诊室接受镰状细胞痛治疗的患者入院的可能性是去输液中心治疗的患者的两倍多。
安东尼将诊所的作用描述为变革性的。
“这就是它如何帮助人们掌握他们的治疗。”她说。“你知道,在急诊室里,他们会被推到一边,告诉他们会没事的。但在输液中心,他们立即得到治疗,感觉更舒服。”
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还在研究使用丁丙诺啡治疗镰状细胞病患者的复杂慢性疼痛。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佩克和安东尼都认为,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这很重要。
Pecker说:“我不认为镰状细胞病患者或他们的家人会因为他们所拥有的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所经历的难以置信的痛苦而得到认可。”“我认为历史也告诉我们,一些真正勇敢的病人做出了深刻的利他主义选择,以帮助其他人改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故事。”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