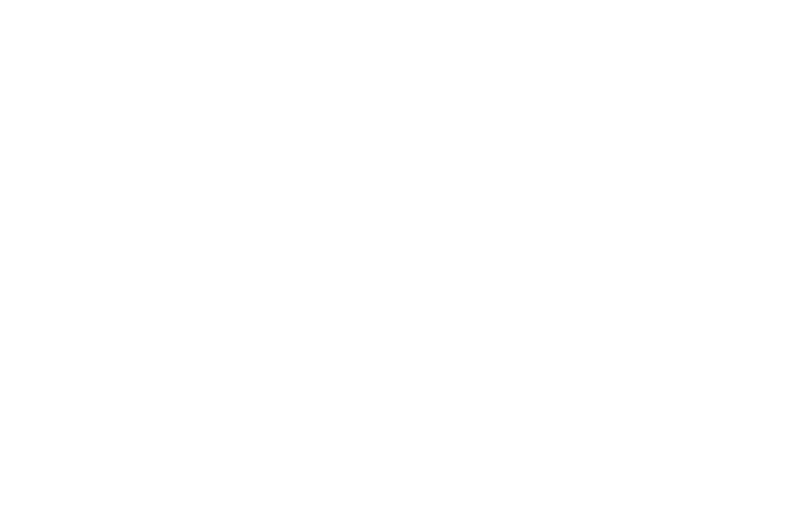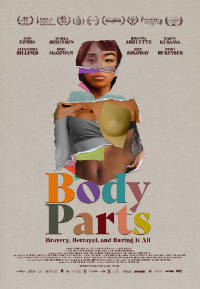编者按:本页于1月30日下午4:50更新,以注明凯西·莱维特为文章中第一条引文的出处。
1974年,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专业研究生凯西·莱维特、米基·格里森和克里斯汀·莱西亚克拍摄了他们的纪录片《我们还活着》(We’re Alive),讲述了被关押在加州妇女机构的女性的故事时,她们对艺术引发改变的力量持乐观态度。
他们希望这部电影能被用于教育、犯罪学、社会学和法律课程,以帮助改变非人性化的状况。唉,这并没有发生。
尽管加州的犯罪率自1997年以来有所下降,但该州还是新建了20所监狱,被监禁的人数增加了800%。被监禁的女性人数激增了475%。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三个学生毕业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而他们的电影却在时间的流逝中湮没了,只在电影档案中留下了几张拷贝。但在1月28日,这部电影的新修复版本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举行了首映式。
莱维特在开场致辞中说:“我们非常感激……尤其是你们今天将在电影中见到的女性。”他们的话在1974年很有影响力,今天仍能引起共鸣。这部电影的奉献精神依然存在。“敬以前所有的女人。给所有的女人。现在是女人的事了。’”
此次放映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电视资料馆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女性研究中心芭芭拉·史翠珊中心合作举办。电影上映后,曾在加州妇女机构(California Institution for Women)工作过的活动人士加入了电影制片人的行列,讨论了20世纪70年代监狱条件与当前加州监狱生存现实之间的连续性。
拯救一部“孤儿”电影
能够举办这场关于这部48年前的电影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包括彻底寻找所有现存的印刷品(幸好英国电影学院有两张)和大量的修复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弄清楚是谁制作了这部电影,因为屏幕上的演职员表上只写着:“加州女性学院的视频工作室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女性电影工作室。”
幸运的是,命运眷顾了我。凯西·莱维特(Kathy Levitt)参加了202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保护节(UCLA Festival of Preservation),在与资料馆电影策展人托德·维纳(Todd Wiener)聊天时,莱维特提到她和两位艺术硕士同学一起拍摄了《我们还活着》(We’re Alive)。
“我们惊呆了,”资料馆馆长洪哈阳(May Hong HaDuong,音)说,她的工作人员领导了《我们还活着》的修复工作。
电影制作人告诉观众,他们没有提到她们的名字,因为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她们的,而是关于这些女性的故事。匿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参与的女性。虽然监狱允许学生们领导视频研讨会,但他们不应该制作公开放映的电影。
在49分钟的放映中,观众被这些被监禁的女性直率而诚实的声音所吸引,她们全面而细致地讲述了监狱生活,以及她们对系统性不公的看法。他们详细描述了自己劳动得不到报酬(如果有工资的话,每小时7到10美分)的挫败感,并不断受到记录任何违反规定的威胁(包括因病不能工作)。她们分享了社会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对女性监禁的影响。
“我们为压迫者付出代价。我们支付工资,”一名妇女在影片中说。“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去上班,是为了支付那些把我们锁起来的人的薪水。”

但他们也谈到了他们个人和集体建立社区的力量,以及被允许穿自己的衣服而不是囚服的尊严。
“我知道在监狱里,团结会更强大,因为你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影片中的另一名女性说。“当你在自由的世界里,这似乎有点自私。人们似乎不太关心其他人。所以我很好奇——到底谁在坐牢?真的是我们吗?”
在修复后的电影首映后,史翠珊中心政策和社区研究副主任科尔比·伦茨(Colby Lenz)主持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与格里森、莱西亚克和里夫特一起登台的还有罗玛琳·拉尔斯顿和苏珊·布斯塔曼特,她们都是加州女性囚犯联盟的成员,都曾在加州女子监狱被监禁过。
在讨论的早期,Lesiak谈到了她从这些女性身上学到的东西,以及她仍然坚持的东西。
Lesiak说:“这部电影中的女性是一种相互关心的姐妹情,这种姐妹情在外部世界中是不存在的,是如此支离破碎。”“那么谁真的在监狱里呢?”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被监禁了20多年的人,拉尔斯顿说,她非常钦佩《我们还活着》如此诚实和完整地描绘了这些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她们如何获得了一个平台来谈论贫困、药物滥用、种族主义和法院是如何导致这些女性最终入狱的。
“这不是社会对监禁和被监禁的人的看法,”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反弹项目”执行董事拉尔斯顿说,他在2022年获得了州长加文·纽森的完全赦免。“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直到今天,那些目前被监禁的女性仍然存在。”
她接着说:“缝纫工厂的血汗工厂,以及它对心灵的影响,以及它如何塑造一个人的存在,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是那些工作。他们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不想当看门人。我不想当厨师。我不想当裁缝。我不想做指甲。我不想做头发。我还能做别的事,也已经做了别的事。”
布斯塔曼特被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赦免,在服刑31年无假释终身监禁后,于2018年从加州妇女机构(California Institution for Women)获释。布斯塔曼特指出,最低时薪仍然没有变。
“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一切都没有改变,”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太多事情变得更糟了。”
布斯塔曼特是监狱里被判有罪的妇女反对虐待组织的创始成员,也是加州女性囚犯联盟的长期成员。布斯塔曼特目前是“自由家园”(Home Free)的重返教练,这是一个针对长期监禁后即将回家的家庭暴力幸存者的项目。
倡议者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布斯塔曼特指出,监狱中越来越多地使用隔离措施,这阻碍了妇女形成社区。她说,这反映了强调惩戒制度惩罚性方面的整体趋势。
布斯塔曼特说:“有一段时间,有几个州长说,‘无期徒刑者不会离开,除非被关在松木盒子里。’”布斯塔曼特一直积极参与让加州废除无假释终身监禁的运动。“你能想象这让你有什么感觉吗?”
尽管变化不大,但莱维特说,拍摄这部电影的经历仍然改变了她。“这些女人和她们的声音,”她说,“这些年来一直伴随着我。”
布斯塔曼特分享了一个好消息:超过200人的无假释终身监禁被减刑并获释。“零累犯。所以没有人犯罪。”
当晚还播放了电影制作人奇萨·休斯(Chisa Hughes)拍摄的一段短视频,她记录了加州目前结束无假释生命的努力。尽管监狱的条件几乎没有改变,甚至恶化,但艺术家/活动家的奉献精神依然存在。
“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资料馆修复和保存这类材料时,他们给了今天和未来的学生一个很好的机会,真的,看到参与政治的女性,”格里森在放映前说。“我觉得这太神奇了。”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