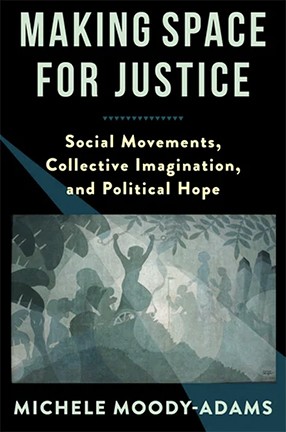哲学教授米歇尔·穆迪-亚当斯(Michele Moody-Adams)在平等和社会正义、道德心理学和美德以及性别和种族的哲学含义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
从19世纪的废奴主义到今天的黑人生命很重要,进步的社会运动一直处于社会变革的最前沿。然而,人们很少认识到,这种运动不仅参与政治行动,而且还就正义的意义以及如何满足正义的要求提出了关键的哲学问题。 在《为正义创造空间:社会运动、集体想象和政治希望》一书中,约瑟夫·斯特劳斯(Joseph Straus)政治哲学和法律理论教授、哲学系主任米歇尔·穆迪-亚当斯(Michele Moody-Adams)认为,任何关心正义理论或实践的人都必须问,从社会运动中可以学到什么。
她通过一系列例子,探讨了社会运动对正义本质的了解,以及为世界正义创造空间需要做些什么。穆迪-亚当斯认为进步的社会运动是道德探究的源泉,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提出了关键的哲学和实践原则。《为正义创造空间》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见解对于弥合挑剔的理论与有效实践之间的差距至关重要,并且应该对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主义产生变革。
穆迪-亚当斯与哥伦比亚新闻讨论了她的书,以及为什么她的惊奇感最近被诗歌所丰富,以及为什么她想退休到大苏尔。
问: 是什么激发了你写这本书的灵感?
答: 首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观察,即“社会进步永远不会在不可避免的车轮上滚动”,而只能通过敬业的人的不懈,苛刻的工作来实现。這本書部分地是為了了解普通人在追求正義時願意忍受的工作和非凡的犧牲的努力。
当这些牺牲建设性地改变社会世界时,这几乎总是因为社会运动利用人类重新想象世界的能力,并帮助他人理解根据看待和思考社会生活的新方式重塑世界的可能性。所以,我灵感的第二个来源是人类想象力的力量。我探索了社会运动如何利用这种力量——在美学行动主义、语言行动主义和叙事行动主义中——来帮助为正义创造空间。
第三,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谋杀引发的全国性和全球抗议活动最直接地激发了我把我的反思放在目前的形式上。随着2020年夏天的进展,这些抗议活动帮助将愤怒和绝望转化为政治上强有力的希望,我想对这种希望的本质和来源进行哲学上的反思。运动参与者如何维持政治希望——并经常激励他人——即使面对深深的失望,有时甚至在他们面对强大的倒退反弹运动时?通过探索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希望和恐惧的作用——来回答这个问题。
问:你能举例说明社会运动如何弥合理论与实践以及政治思想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差距吗?
答: 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部分原因在于产生更具洞察力的理论。我认为,大多数成功的社会运动都产生了参与式的道德探究,通过对不公正经历的细致理解,加深了我们对正义要求的理解。这本书表明,从参与的道德探究中得出的最重要见解之一是,我们有责任不把目光从不公正中移开: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所敦促的那样,“在面对不公正之前,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埃米特·蒂尔的母亲在1955年坚持在她儿子的葬礼上要一个打开棺材,并确保他的尸体被媒体拍摄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从1958年到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正确地认为,除非世界被迫面对针对非暴力抗议者的身体暴力的令人不安的形象,否则吉姆·克劳(Jim Crow)的种族隔离不会结束。
但是,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有效实践时,我们才能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人们很容易认为,社会运动的方法主要是静坐、游行、抵制和各种公众抗议。为正义创造空间表明,最有效的社会运动已经认识到需要其他方法,如叙事行动主义(如19年奴隶叙事的写作和传播)。(千)-世纪废奴主义),语言激进主义(如在20中性骚扰概念的发展(千)-世纪妇女运动)和审美行动主义(如21(圣)- 抗议者试图从公共荣誉场所移除非人性化纪念碑的世纪努力)。
问: 你最近读了哪些书,你会推荐,为什么?
答: 在《狄埃特书》中,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断言,哲学始于惊奇。最近,我发现我的惊奇感通过阅读诗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尤其是艾米莉·迪金森和玛丽·奥利弗的诗歌。我正在浏览奥利弗的两卷本发光诗集《新诗集》和《诗选》。 我最熟悉的狄金森诗歌版本是1960年的一卷诗集,由托马斯·约翰逊编辑。 作为一名阅读奥利弗和狄金森非凡诗歌的哲学家,我确信现在是时候在哲学和诗歌之间古老的争吵中呼吁休战了。
问: 你床头柜上现在有什么?
答: 我为快乐而做的阅读分为两大类:回忆录(广义上,包括自传)和关于电影和电影制作的书籍。
最近让我感到惊讶和吸引我的一本回忆录是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告别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因为它在个人和政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以及他写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恐怖的尖锐幽默和道德敏感性的结合。我剛剛開始閱讀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的《天主教少女紀記》(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我最初被這本書所吸引,是為了了解麥卡錫的父母在1918年流感流行中去世後,她的生活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我希望接下来能读一读艺术学院写作教授玛戈·杰斐逊(Margo Jefferson)的《黑人》(Negroland),部分原因是我和杰斐逊一样是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但主要是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她的回忆录写得非常出色。
关于电影和电影制作的书籍变得很重要,因为我正在考虑开发一门关于哲学和电影的本科课程。由于我是《红鞋》和《黑水仙》等电影的粉丝,我刚刚读完了安德鲁·摩尔(Andrew Moor)、《鲍威尔》(Powell)和《普莱斯伯格》(Pressburger: A Cinema of Magic Spaces)的一本书。我还在读几本哲学家关于电影的书,包括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的《道格拉斯·瑟克:电影制片人和哲学家》(Douglas Sirk: Filmmaker and Philosopher)。Sirk在1959年翻拍的《模仿生活》(Imitation of Life)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皮平(Pippin)对这部电影如此独特的原因进行了启发性分析。
问: 你有没有一本别人都没听说过的最喜欢的书?
答: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可能在电影制作人世界之外并不为人所知——沃尔特·默奇(Walter Murch)的《眨眼:电影制作视角》(In the Blink of an Eye: A Perspective on Filmmaking)。 2016年执导电影《月光男孩》(Moonlight)的巴里·詹金斯(Barry Jenkins)称赞了默奇的书,因为它教会了他关于电影编辑和电影制作的知识。但《眨眼之间》也是关于情感在电影制作和观看中的作用,关于我们如何感知和思考世界(在电影内外),以及讲述一个好故事是什么。
问: 有什么令人兴奋的夏季计划吗?
答: 我很高兴在大流行期间无法前往加利福尼亚中部海岸。二十多年来,我们一家人至少在圣克鲁斯,蒙特雷和大苏尔度过了几个夏天的一部分,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事实上,如果我有我的德鲁特,我会在大苏尔退休 - 尽管野火,泥石流和地震的威胁不断。退休不太可能发生,但至少我可以沿着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旅行,享受世界上最美丽的海岸线之一。
问: 您正在举办晚宴。你会邀请哪三位学者或学者,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你会邀请,为什么?
答: 很难将名单保持在三个,但我最想邀请詹姆斯·鲍德温,托尼·莫里森和阿尔伯特·加缪,因为他们了解文学挑战和启发我们的力量,因为他们欣赏社会思想的必要性,依靠想象力来激发希望,即使在失望面前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是,对话肯定是生动活泼和具有挑战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