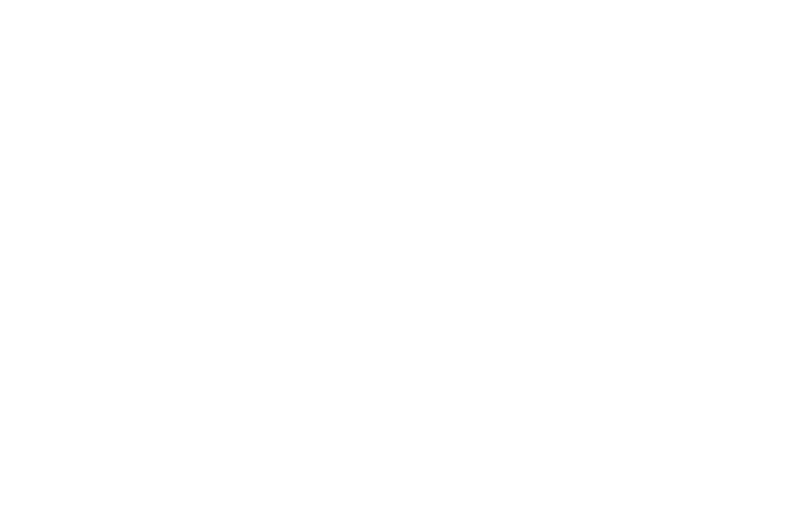在过去的20世纪,人们不可避免地认可了如此多的女性艺术家,她们仅仅被视为缪斯、情人、妻子或伴侣,而她们的作品确实像她们的伴侣一样强大、美丽和原创,朵拉·马尔(Dora Maar)由于许多原因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
Maar原名Henriette Théodora Markovitch, 1907年生于巴黎,1997年7月16日去世。她的母亲是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乡亲妇女,她的父亲是一位流亡的克罗地亚建筑师,他们在阿根廷生活了20年,但从未在经济上取得成功。
Maar发现了摄影
一家人回到巴黎后,玛尔学习了绘画和装饰艺术,然后把相机作为她的谋生手段和艺术表达手段。时尚摄影,不寻常的肖像——她的作品如此广泛,在1931年,甚至在她25岁之前,Maar已经和布景设计师Pierre Kéfer一起拥有了一个成功的工作室。
Maar随后开设了一个个人工作室,在那里她创作了一些最著名和最令人兴奋的蒙太奇照片。最著名的可能是Ubu Roi(1936),一个奇怪的,非人类生物的代表,一种犰狳胎儿-她从来没有想要表明这是哪种动物,以免失去它的神秘- André布雷顿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trouvé(现成的)。
《杜布肖像》,朵拉·玛尔,1936年。Adagp,巴黎/ Philippe Migeat - Centre Pompidou, MNAM-CCI /Dist。RMN-GP
此外,阿斯特格街29号(1936)也是超现实主义摄影的一个明显例子,其中不同大小、位置和现实的元素混合在一起,《明星假人》(1936)也是如此。其他一些蒙太奇照片,比如迷失在无尽迷宫中的孩子和女人,或者被泥泞和雨水侵袭的资产阶级房间,也都是她的杰作。
在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玛尔和其他摄影师如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一样,轮流描绘富人和名人,时尚和奢侈,描绘当时存在于巴黎的肮脏和贫穷。Maar当时的照片与Brassai、Eugène Atget等人的照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客观或纪实的方面在他们身上并不占优势,而是我们后来在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等摄影师的作品中发现的对象征主义和怪诞的追求。
1932年,Maar前往巴塞罗那,拍摄了这座城市的街头生活。她还为穷人拍摄粗糙的肖像。
1933年朵拉·马尔(Dora Maar)在巴塞罗那拍摄的几张照片蒙太奇,最近被加泰罗尼亚国家美术馆(Arxiu Nacional de Catalunya)收购。Arxiu Nacional de Catalunya
她的工作引起了当时社会的注意。她很快就被邀请加入巴黎最先进、最现代的圈子:超现实主义。在这种环境下,她是作家乔治·巴塔耶的情人,雅克的朋友Prévert和保罗的朋友Éluard,以及André布雷顿的第二任妻子杰奎琳·兰巴的密友。事实上,兰巴和布雷顿可能是通过马尔认识的。
超现实主义将Maar从摄影中外表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允许她表达一种狂野的精神,嘲笑一切,包括,也许最重要的是,她自己的恐惧。
进入毕加索
Maar与毕加索相识于1935年,也就是西班牙内战爆发的前一年。除了她的身体和智力的辉煌,这位出生在马拉加的艺术家无疑还被她说一口完美的西班牙语所吸引。
与奥尔加·乔洛娃结婚,并与年轻的情人Marie-Thérèse沃尔特配对,毕加索疯狂地爱上了玛尔。她在café上玩着用刀割伤自己的游戏,引起了画家的注意,画家偷走了她当时戴的带血的手套。毫无疑问,这是一段不祥关系的开始。
当她成为毕加索奇怪圈子的一员时,她的职业生涯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
她和毕加索一起生活了八年。对于这位艺术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非凡的时期,在此期间他画了许多最好的作品,包括马尔的肖像。她用照片记录了格尔尼卡的建设“过程”,这是一项非凡的壮举。这在当时是完全创新的,并引发了许多其他摄影师的作品,如汉斯·纳姆斯与波洛克,或克鲁佐与毕加索本人,但Maar的独创性仍然没有得到认可。
朵拉·玛尔关于格尔尼卡创建的报告文学的一部分。雷纳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Sofía
毕加索还和玛尔一起在底片上作画,但后来坚持让玛尔放弃摄影,全身心投入绘画——在他看来,绘画是“伟大的艺术”。最后,毕加索带领玛尔进入了他绝对主导的领域。
必须指出的是,她努力创作个人作品,尽管她的一些作品受到毕加索艺术的影响,但它们本身就很有趣(例如1937年的《对话》)。但要在毕加索独领风骚的领域里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
1945年,马尔创作了毕加索风格的静物画,后来又创作了一些肖像画,主要是女性,让人想起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如莱昂诺尔·菲尼。
与毕加索一样,这是一段新的恋情,这次是与年轻画家Françoise Gilot,结束了一段异常有毒的关系,Maar濒临疯狂,毕加索对她进行了令人震惊的虐待。
第三幕
Maar被关在精神病院,接受电击,并接受当时可怕的心理治疗,这对精神分裂症和心碎或抑郁症都有好处。多亏了诗人保罗Éluard,他向毕加索寻求帮助,Maar成功地离开了这个机构。她接受了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治疗,然后开始隐居,全身心投入绘画,并在天主教神秘主义中寻求解脱。于是,她的名言诞生了:“毕加索之后,只有上帝。”
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的绘画转向了抽象,尽管与风景密切相关,高度涂布的作品完全背离了毕加索的艺术,但并不是很有趣。
玛尔对毕加索的巨大情感依赖,她绝望的极端表现,意味着她的形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剥夺了伴随她早期成功而来的辉煌和她作品的复杂性。
著名的历史学家如玛丽·安·考斯(Mary Ann Caws)和维多利亚(Victoria Combalía)亲自认识她,他们的著作让她走出了默默无闻的状态。渐渐地,一些展览,比如2019年泰特美术馆的展览,恢复了她的名字和她在艺术史上的遗产。第三幕正在上演https://youtu.be/L_VLDL1omaI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