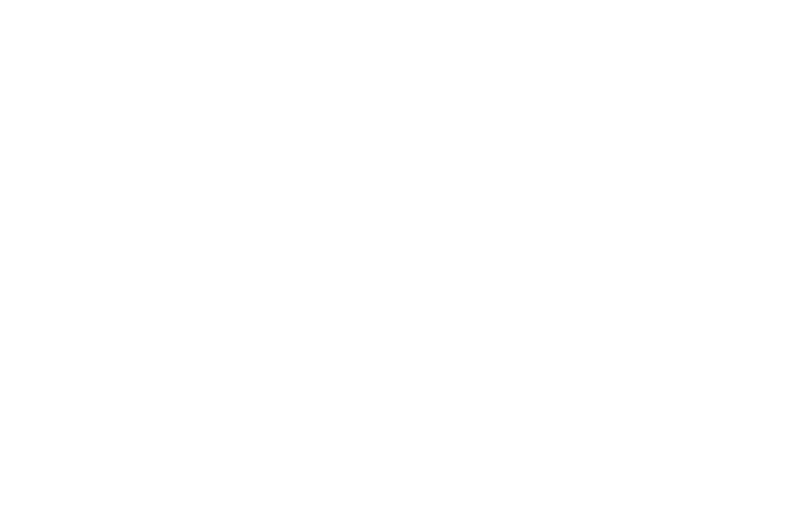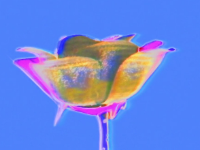除了橄榄球和火鸡,感恩节还有另一项经久不衰的传统:与投资者相对。每个家庭都有一个这样的人——不守规矩的人,他们的大声意见让假日餐桌上的讨论戛然而止,每个人都突然低头盯着他们的土豆泥。你要么参与,冒着激烈的争论只会进一步破坏这个场合的风险,要么翻白眼,避免接触,从一年只有一次的知识中寻找安慰。
但现在有一个更发人深省的想法: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每天都能遇到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亲戚、同事甚至朋友的时代,那该怎么办?
努力在一个特别危险的时刻重建日常互动。YouGov和《经济学人》去年夏天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令人震惊的是,40%的美国人认为内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爆发。即使你和60%的人一样,认为未来不那么反乌托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政治超负荷的时代。
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们如何才能做得更好——用同情来缓和激情,避免因为“对方”的想法与我们不同,就认为他们本质上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幸运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些聪明的人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都怪大脑
部分问题可能出在我们的线路上。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马修·利伯曼(Matthew Lieberman)分析了此前关于这一主题的400多项研究,发现大脑中有一个被他称为“完形皮层”的区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模糊或不完整的信息,并排除其他解释。它会使我们把对人和事的主观理解误认为客观事实。他说:“我们往往对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抱有非理性的信心,当别人看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不同时,我们就会认为他们是被误导的、懒惰的、不讲道理的或有偏见的。”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美裔政策与政治研究所(UCLA hispanic Policy and Politics Institute)主任索尼娅·迪亚兹(Sonja Diaz)指出,在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共享和吸收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过去常常去图书馆,读纸质报纸,打电话。”她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邪恶利益集团的混合体,无论是有钱的政府还是外国政府,它们正在围绕真相和治理塑造叙事。”其结果是,曾经令人尊敬的政治分歧如今变成了围绕基本事实的激烈冲突。“我们交流的速度已经改变了我们获取内容的方式——由于社交媒体没有监管,这些内容是不受限制的,”迪亚兹说。这些渠道“不仅能说服一个人,而且能说服成千上万的人相信一些事实是错误的。”
迪亚兹补充说,在大众媒体中,叙事几乎总是被框框成“我们对抗他们”,这未能反映出这个国家复杂的多样性。她说:“由于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虚假信息,故事本质上是有权利的人与那些接受权利的人的斗争,而种族-社会结构使许多社区在寻找共同点时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家Lynn Vavreck和Chris Tausanovitch领导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小组每周都会采访6000人,以捕捉总统竞选期间的公众舆论动态。然而,尽管经历了大流行、经济危机、一场不同寻常且竞争激烈的白宫竞选等重大事件,人们的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
在他们的新书《苦涩的结局:2020年总统竞选和对美国民主的挑战》中,瓦夫莱克和她的合著者认为,美国政治的这种“钙化”是四个关键发展的副产品。前两种情况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发生:两大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距离越来越远,而这些政党内部也趋于同质化。第三次和第四次是最近发生的。第三个发展是,与过去在税收或政府角色和规模等问题上的冲突不同,今天最大的政治问题往往更加个人化:移民、堕胎、性别、种族、民族、宗教。Vavreck说:“这些(问题)自然会引起更多分歧,因为它们关乎权利、平等以及作为美国人的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第四个发展——选民中不同寻常的党派平等程度,这迫使两党在失败后坚守阵地,而不是重新评估自己的立场。Vavreck总结道:“当你把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时,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对方’与我们是如此‘不同’,我们是在为受到身份影响的问题而斗争,而胜利总是触手可及。”
“我们总是会在政治上分裂。”Efrén Pérez说,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种族、民族、政治和社会(REPS)实验室的政治学和心理学教授。他说,新的是最近围绕我们的分歧而出现的社会规范的崩溃,这最终为2021年1月6日对美国国会大厦的袭击铺平了道路。“政治辩论过去是庄严的。”Pérez说。“现在大家都在大喊大叫,互相抨击,听起来好像你是对的,而不是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
Pérez指出,为了激励选民,政党试图妖魔化造成社会弊病的群体。“双方都在利用这些偏见,因为这很有效。”他说。“当非西班牙裔白人说,‘这不是我过去所了解的国家’时,这不是开玩笑——我们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他们在社会中失去地位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因为对他们不利的制度,但必须让人感觉是这样的。”
正如Pérez所看到的那样,好消息是:“规范可以重新建立和重新配置。我们不应该只以我们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个人,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群体。当你表达你的观点时,你是谁?你想成为那样的人吗?”
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科学家马可·亚科博尼(Marco Iacoboni)也认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共情危机。“同理心是连接我们的东西。”负责Ahmanson-Lovelace大脑测绘中心神经调节实验室的Iacoboni说。“一个社会如果不理解他人的观点、信仰和愿望,就不可能存在。”
Iacoboni的神经成像研究有助于阐明产生同理心的大脑机制。镜像神经元是一种细胞,当我们感受到一种情绪或执行一个动作时,以及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表现出这种情绪或执行动作时,它们就会被激活;例如,当我们看到别人疼痛时,正是这些细胞促使我们退缩。但其他与理性反应联系更紧密的细胞,也有助于实际行为。如果我们被情感同理心所淹没,我们就无能为力。认知同理心让我们关闭情绪控制的时间足够长,以提供帮助。
因此,Iacoboni认为,如果我们被另一个人的观点冒犯了,认知同理心可以转移这种敌意,让我们参与更有成效的对话。他说:“与想法不同的人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试着理解对方的观点,这会让你更富有同情心。”
也就是说,一旦我们离开了自己的社会群体,同理心水平就会急剧下降。但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群体是全人类呢?亚科博尼说:“我们可以在食物和家庭等基本问题上与任何人联系。”“如果我们先谈谈我们共有的东西,等到我们谈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另一种观点。”
这也意味着要逃离“回音室”,在那里,你自己的信念会不断地反射回你,并得到强化,从未受到深思熟虑的挑战。
没人能指责乔亚·Leap没能走出自己的幻想。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工作者,Leap领导着鲁斯金公共事务学院的社会正义伙伴关系,她与现有和前帮派成员合作,她的部分工作是帮助那些在监狱系统中准备重返社会的人。她的丈夫马克(Mark)是一名退休的洛杉矶警察,曾担任负责该市反恐事务的副局长。“没有什么比这更奇怪的了。”Jorja Leap笑着说到这对夫妇截然不同的观点。“这是为我们关系中的暴风雨时期而生的。”
这也迫使他们建立一个可以分享观点、倾听和学习的空间。Leap说,她和丈夫学会了通过争论意见分歧来达到对方的立场。她对人类倾向于退回到志同道合的圈子来避免冲突感到遗憾。她说:“认为我们能解决所有分歧是愚蠢的。”“但我们需要对话,这意味着要逃离回音室。”
当遇到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时,Leap会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我被贴上了黑帮专家的标签,但我从不接受这一点。”她说。“我深信我可以向每个人学习。”
对于那些与投资者背道而驰的亲戚和他们的同类,索尼娅•迪亚兹(Sonja Diaz)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建议:“你不能改变任何人,但你可以改变你与他人互动的方式。”迪亚兹认为,我们应该铭记过去几年来我们的集体创伤——在一个获得高质量精神卫生服务的渠道短缺的时代,这是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人们都很紧张,”她说。“我想到的是宽容——通过在与人交往时设置健康的障碍和限制来宽容自己,然后当你选择这样做时,要注意存在的地雷。”
现在请把蔓越莓酱递给我。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