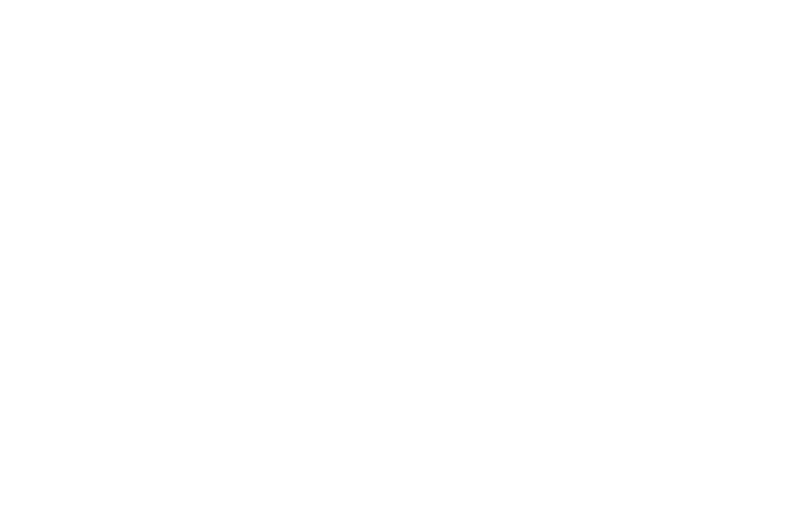本文由西澳大利亚大学澳大利亚文学系主任托尼·休斯-德思教授撰写,最初发表于2022年12月5日的The Conversation。
金·马胡德因她的第一本书《干涸湖的工艺》(2001)的出版而声名鹊起,该书详细描述了她与她成长的土地——塔纳米沙漠的一个养牛场——重新联系的努力。
她的旅程是由她父亲的去世引发的,他在1990年外出集结时死于直升机事故。《干涸湖的工艺》是一本令人着迷的、生动的游记,将作者的记忆和她父亲的信件和记录结合在一起。它是澳大利亚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回忆录作品之一。
《干涸湖的工艺》与华莱士·斯特格纳获得普利策奖的经典作品《狼柳》(Wolf Willow, 1955)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者也讲述了一个人在中年时前往偏远农村边境的童年家园的朝圣之旅。在澳大利亚,它也可能被比作多萝西·休伊特的《外卡》(1990)。当他们回到童年的家时,马胡德、斯特格纳和休伊特意识到他们的家已经不在了。当然,这个地方仍然在那里,但他们起源的准神话性质并没有得到回答,即使是最微弱的迹象表明这个地方还记得他们。
如果马胡德的职业生涯以《干涸湖泊的工艺》结束,我们将会看到他对童年的深刻描述,其中充满了对澳大利亚干旱内陆地区独特生活条件的智慧和洞察力。
但马胡德自1992年第一次回到Tanami以来,她的生活和事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一直在回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在她家以前的养牛场周围的土著社区度过每年的大部分时间。每年的另一半时间,她都在堪培拉的郊区度过,在那里,她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建立了联系。
这种双重生活在马胡德的第二本书《立场怀疑》(2016)中有所体现。这本书保留了一些多余的抒情,这是《干湖工艺》的标志。但《立场可疑者》也表现出对当今沙漠土著社区现实矛盾的更敏锐的认识。
“地面真相”和“深度绘图”
《意图漫步》是马胡德的第三本书,是一本文集,其中一些是新书,另一些最初发表在《格里菲斯评论》、《The Monthly》和《最佳澳大利亚随笔》上。《可疑的位置》表面上是一部地图制作作品,而在《意图漫游》中,马胡德发现自己在反思自己试图制作的地图。
他们从土著居民开始,他们的知识体现了真理的一个维度,这往往是最精确的地图所无法理解的。就像作家兼学者保罗·卡特一样,马胡德提出了“地面真相”的概念,认为地图只有在被迫与生活在地面上的人的记忆和理解发生碰撞时才会收集到真相——也就是说,在大脑虚拟地图的笛卡尔平面之外的某个地方。
在我看来,实地考察是从一个地方的物理属性开始,然后再转向那里发生的事情。它把人放在合适的位置,这就带来了科学、故事、畜牧业、历史、隐喻和神话。这种形式的制图被称为各种各样的东西——共同制图、跨文化制图、反制图、激进制图。作为文字大师,我喜欢激进制图的华丽暗示,但我的扯淡探测器却觉得它矫情。我做的事一点也不激进。唯一令人惊讶的是,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做过。
在北美,马胡德从事的这种制图有时被称为“深度制图”,这是历史学家威廉·莱斯特·热·穆恩(William Least Heat-Moon)开创性的工作。这个概念最近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流行起来。
在《意图漫游》一书中,我们看到马胡德描述并反思了她参与的一些深度测绘项目。其中包括与东皮尔巴拉的马尔图人合作的展览《我们不需要地图》(2012年),以及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的《歌行:追踪七姐妹》(2017年)展览。原住民艺术的功能是地图,这是本书中有趣的论点之一。
在解释她上一本书的书名时,马胡德指出,“位置可疑”是一个绰号,通常是指澳大利亚沙漠粗略地图上的点。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她强调了认识论的不确定性,这标志着地图所宣称的知识的局限性。
然而,在最新的系列中,马胡德公开承认,这实际上是她自己的立场,以及任何敢站在她立场上的人的立场——这一点值得怀疑。她一直意识到,在她的生活和写作中,她走着一种特殊的边缘。
但是,当我写我与那些在我生命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人和国家的互动时,我走过的边缘变得越来越稀薄和尖锐。对白人读者来说,遥远的土著世界代表着从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到悲惨的反乌托邦的一切,但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达到了自己的说实话标准。这变得越来越难做到。
随着这条边缘变窄和变尖,它开始像它曾经被称为边界的东西。边疆的概念本质上是帝国的,因为它引发了目前的征服程度。但边界一直是交流的地方,在那里,公开的权力差距常常令人不安地消失。
政治与行政
这正是马胡德的作品所擅长表现的。《有意漫步》收录的文章包括当代经典之作,如《吹在寒冷的沙漠风上》(2007年)和《卡蒂亚就像丰田车:澳大利亚文化前沿的白人工人》(2012年),这两篇文章都最初发表在《格里菲斯评论》上。这些文章描述了存在于西部沙漠偏远社区的结构性混乱,在那里,土著居民生活在他们不断发展的世界里,毗邻澳大利亚政府机构。
马胡德能够描绘的,往往是那些在偏远社区从事管理“政府服务”工作的人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她还戏剧化地描述了经常伴随着这些日常遭遇的根本不匹配。事实证明,当地土著人民的愿望往往与澳大利亚政府的愿望截然不同——即使后者会随着政策和政治的风而摇摆不定。
妥协达成,讨价还价达成,交易破裂,物品出借或丢失,提供补偿,等等。对土著人民来说,这只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生活结构,但对介入的行政人员——卫生工作者、学校教师、警察——来说,这往往是一种深刻的幻灭之源。他们感觉被背叛了。但殖民者是如何成为受害者的呢?
马胡德公开描述这些情况值得称赞,她的作品对于任何希望了解澳大利亚边境如何绝非过去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她早年写回忆录时的那些浪漫时刻,已经渐渐被她认真对待当下的意愿冲淡了——简而言之,活在当下。
如果是一个缺乏实际智慧的人,玩世不恭就会占上风。事实上,有时马胡德似乎被赫里奥的鬼魂所困扰,赫里奥是伦道夫·斯托的《到群岛去》(1958)中金伯利传教中幻想破灭的牧师。马胡德和斯托都在战后离开了车站生活的童年,进入了珀斯著名的私立学校。
然而,与赫里奥不同,马胡德并没有陷入形而上的危机。她也没有放弃对沙漠生活和文化深度的感受。她知道她的深刻与她的土著同伴不一样,但直觉地认为,只有认真对待生活的实用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锻造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我写的是在交叉点上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传统文化仍然强大,白人是少数,但占据了大部分的官方职位,在那里,展开的叙事是复杂的,微妙的,不断演变的[…]当我写沙漠土著居民时,我行使了文化特权,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问题是我是否以正当的方式行使这一特权。自从我开始写作以来,我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难题,而且从来没有变得更容易过。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许可,从The Conversation重新发布。阅读原文。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