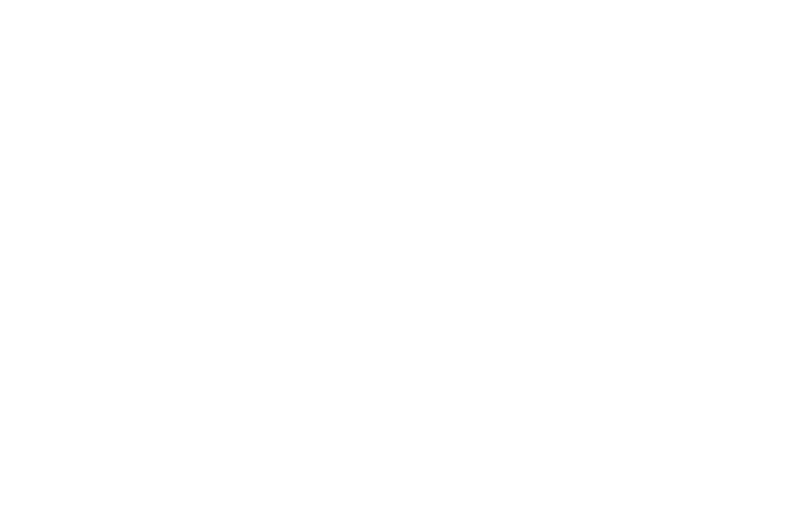多米尼加出生的作家简·里斯的生活既为人所知又神秘。她的职业生涯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段跌宕起伏,经历了名字的变化(Ella Gwendoline“Gwen”Rees Williams, Ella Lenglet, Jean Rhys)和地点的变化(西印度群岛,英格兰,欧洲)。
她成年的早期生活很充实。她曾在舞台上担任合唱舞蹈演员,与富有的男人交往,嫁给了一个迷人的荷兰重婚者和骗子,这让她去过海牙、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她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带领下出版了她的作品,她经历了一阵文学上的名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他们后来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后来她被遗忘了,她的都市故事似乎与战前和战时的黑暗过于残酷地契合,出版商拒绝了她的作品,读者认为她一定已经死了。
随着她最著名的作品《广阔的马尾藻海》(1966)的出版,她的命运发生了辉煌的逆转:这是对简·爱的重新想象——甚至是重新梦想——作为第一任罗切斯特夫人的生活,一个白人克里奥尔人。随之而来的是愤怒的晚年。里斯靠喝酒(但也用魔法)度过了多年的贫困,依靠朋友们顽强而勇敢的慷慨生活。
每一次重新出现似乎都是不同的作家:一个女人,一个现代主义者,最后是西印度群岛人。
渡水
里斯的生活细节是通过两部传记为人所知的:卡罗尔·安吉尔大受好评的《让·里斯:生活与工作》(1985)和莉莲·皮奇奇尼轻松的《忧郁的时刻:让·里斯的一生》(2009)。但它的轮廓也让人耳熟能详,因为它与那个世纪许多女作家的文学生涯中错误的或晚开始的,或被迫停止的情况相呼应,在这些情况下,文学声誉成为变幻莫测的文学品味和家庭责任的牺牲品。
2018年,圣基茨出生的作家卡里尔·菲利普斯出版了一本基于里斯前46年生活的小说。《日落帝国》讲述的是1936年格温·威廉姆斯和她无精打采的英国丈夫回到多米尼加的故事。然后跳到她的童年,她从小岛到灰色的英格兰的旅程,跳过了她在巴黎的岁月,并在她第二次离开时结束。在船上,她转身离开丈夫:“她的岛屿安排了她,又重新安排了她,她无话可说。”
这部小说将里斯的旅程转向内心,把它变成了失去、衰落和回归的编年史。当她在家族殖民历史的残迹中漂泊时,周围的人把年轻的格温描绘成一个远远不是英国孩子的样子:“在我看来,关德林小姐介于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
2018年,菲利普斯在小说出版时接受了采访,他花了很长时间谈到了写这本书的动机,里斯的西印度群岛故事对他的吸引力。他曾在2011年形容这是“经常将流亡的痛苦与文学的快乐连接起来的脐带”:“穿越水”的共同经历。
菲利普斯几十年前就读过里斯的作品。他曾欣赏过《宽阔的马尾藻海》,尽管这并不过分。但他被1934年的《黑暗航行》(Voyage in the Dark)所驱使,这本书揭示了“英国如何对你的身份发起秘密攻击”。这本小说是西印度评论家肯尼思·拉姆昌德(Kenneth Ramchand)传给他的——“我认为你应该读读这本书”——由此开始了与里斯的作品“更亲密”的关系。
亲密关系很重要。它将菲利普斯的小说与加勒比地区关于里斯的写作遗产联系在一起,并对里斯做出回应。这包括德里克·沃尔科特、洛娜·古迪逊和贾麦特·金凯德等作家的作品,他们很重视里斯对失去、语言和想象的特殊性的描写,因为他们站在“英语传统的边缘”。
他们不能“假定那些处于中间地位的人能够理解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不得不)压缩句子”。例如,里斯对“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选择必须非常清楚,因为英国的出版商没有他们的经验。例如,她看到了不同的日落。”
菲利普斯认为,那些不同的日落没有出现在里斯的传记中。他觉得《安吉尔的故事》完全没有描写“里斯生命的前16年”;她没有意识到里斯是“一个你必须通过加勒比海才能了解的人”。
尽管安吉尔做了如此细致的研究,但她从未去过里斯的家乡。所以菲利普斯亲自踏上了旅程,沉浸在岛上的“质感”中:
多米尼克闻起来像什么?不像英国。当你回去的时候,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空气的沉重质感。加勒比海的夜晚听起来不像巴黎的夜晚[……]感受白天长短的方式不同,你的生活节奏也不同。
20世纪70年代,简·里斯(左)和莫莉·斯通纳。维基共享
多米尼加人的故事
米兰达·西摩(Miranda Seymour)在2018年6月点评了菲利普斯的小说,她写了一本备受好评的简·里斯传记。她将其描述为“偶尔出色”和“善意但有点令人不满意”。她似乎误以为那是一本传记。她发现它“利用里斯的生命”是“反复无常的”:
我们对她的作品了解甚少,对她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关系也一无所知。
这篇评论以小说中里斯第二次离开多米尼加,在1936年回到英国时再次渡水的想象性身份识别为结尾:
菲利普斯告诉我们,小说家简·里斯(Jean Rhys)的作品以冷酷无情著称,她“从自己的心中切下一块,轻轻地扔进蓝色的水中”。哦亲爱的。
尽管西摩反对菲利普斯的风格和方法,但她似乎确实被这部小说所揭示的多米尼加故事所吸引。就像四年前菲利普斯的小说一样,她的传记《我曾经住在这里:让·里斯的噩梦生活》将注意力转向了多米尼克的意义和里斯生命的前16年。在她的前言中,她写道,她不是被里斯的小说所吸引,而是被《请微笑》(1979)所吸引,这是一部晚期的自传体小说集,它唤起了那些岁月和地点。
和菲利普斯一样,西摩也去了多米尼加,在那里她看到里斯家的房子长满了热带植物,并与一些人谈论了该岛、它的过去,以及里斯·威廉姆斯家族在那里的复杂关系。这为她讲述里斯的家庭生活和早年的故事提供了支持,这是对一个世界的生动描述,正如里斯在《黑暗航行》中写道:
一切都是绿色的,到处都在生长[…]绿色,还有绿色的味道,还有水、黑暗的土地、腐烂的树叶和潮湿的味道。
这本传记的开头是让·里斯1963年录制的一首克里奥尔歌曲(数字版本与里斯的论文一起保存在塔尔萨大学麦克法林图书馆),讲述了里斯的生活和渴望,超越了她与欧洲和英国的联系。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这首歌的歌词用她早年不可磨灭的痕迹,任性的威胁,通往魔鬼的道路,控诉了里斯作品中的黑暗性。
Tout mama ki ti ni jen fi -所有有年幼女儿的母亲!
爸lésé yo allé en plési yo, -别让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快乐,
爸lésé yo allé en jewté yo。-不要让他们追逐自己的快乐。
Si diab la vini yi kai anni mé哟。如果魔鬼来了,他只会把它们带走。
Elizé malewé -可怜的Elizé
Elizé malewé -可怜的Elizé
依莉莎malewe。-可怜的Elizé。
On pon innocen la ou van ba de demon la。-你把一个无辜的孩子卖给了两个魔鬼。
西摩收录了这首歌(还有索尼娅·马格洛尔-阿克巴(Sonia Magloire-Akba)提供的翻译,她是克里奥尔语方面的权威,西摩在多米尼加咨询过她),为里斯故事中闪烁的差异性标记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和背景。例如,在英国的寄宿学校,她被戏称为“西印度群岛”。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的《当恶人》(1932)中,她被“诽谤”为“洛拉·波特,一个暴躁而性感的克里奥尔作家”。

但里斯与多米尼加之间的联系并没有真正得到应有的深度,她所处的不同文化和她家族历史上的殖民暴力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深入。这些内容主要局限于本书的前几页。西摩记录了里斯与福特关系的细节和困难,但她没有注意到福特使用了种族化的绰号,将她与她居住的岛屿联系在一起 。
西摩提供了里斯1963年录制这首克里奥尔歌曲的详细记录。她的声音“轻快轻快”;它在档案馆的“尘土飞扬的空气中颤抖”。她停止唱歌。“不太对,”她说,然后又开始,又停下来。她还唱了另一首歌,讲的是一个来自格林纳达的女人被要求“带上她的金耳环,收拾行李回家”。
对西摩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里斯很轻浮,是个“海妖”。但是,当然,它也讲述了一个作家在她的回忆中没有完全正确,漫长而艰难的回忆,难以驾驭的过去以及它的歌曲和故事。
这些为里斯的最后两本著作提供了素材:《睡一觉吧,女士》(1976)和回忆录《请微笑吧》。据卡罗尔·安吉尔(Carole Angier)说,里斯对《睡一觉吧,小姐》(Sleep It Off, Lady)不满意,宣称大多数故事“都不太好”(她在这一点上错了)。

该书出版时,删去了其中一个故事《帝国之路》(The Imperial Road)。在过去的30年里,里斯多次重写了这个故事。在她的档案中有几个版本,其中一个可以在在线期刊《吉恩·里斯评论》上阅读,但它一直没有出版。这是一个关于殖民的回归和拒绝,以及殖民怨恨的故事:一条为纪念英国人在岛上的存在而修建的道路从视野中消失了;然后,当地人就否认了它的存在。
《里斯》的编辑戴安娜·阿西尔删掉了这篇报道,因为它明显支持殖民计划。“我有偏见吗?”里斯在给朋友弗朗西斯·温德姆的信中问道。“我不知道。Dominica对Rhys来说很棘手,但从不直截了当。
尽管对里斯的《多米尼加》很感兴趣,西摩的传记却没有考察殖民关系,而殖民关系是她故事的核心。她写了阿西尔对帝国之路的担忧,但没有写里斯的反思,这是文学学者评论的主题。她还回避了克里奥尔歌曲中非常明显的种族线索。
她描述里斯1936年回到多米尼加的章节充满了迷人的细节,但也有遗漏。她和安吉尔一样,讲述了里斯的哥哥欧文·威廉姆斯(Owen Williams)的故事,欧文和多米尼加女人生了两个孩子。当里斯待在岛上时,孩子们来看望她,但西摩没有透露会面的细节,只提到他们要钱。
然而,关于这个家庭,我们知道的更多。文学学者伊莱恩·萨沃莱(Elaine Savory)采访了其中一个女儿埃娜·威廉姆斯(Ena Williams)。2003年,萨瓦里写道,Ena
她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讲的是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要和她住在一起的教母把她打扮好,这样当里斯-威廉姆斯一家去教堂的路上经过时,她就会坐在房子的阳台上。他们总是不理她。她有欧文的名字,但里斯的白人家庭没有接受她。1936年,里斯与丈夫莱斯利访问多米尼加时,埃娜·威廉姆斯发现里斯善良大方,但她也意识到里斯是受人尊敬的白人社会的叛徒。
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对这位作家,她的家庭,以及她的多米尼加关系,这是一个了解和必要的视角。它提供了一种从岛上的视角,一种超越让·里斯在英国和欧洲生活的尴尬的方式,是她最深刻和最复杂的生活的真实问题。
谈话
布丽吉塔·奥鲁巴斯,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艺术与媒体学院英语教授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许可,从The Conversation重新发布。阅读原文。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