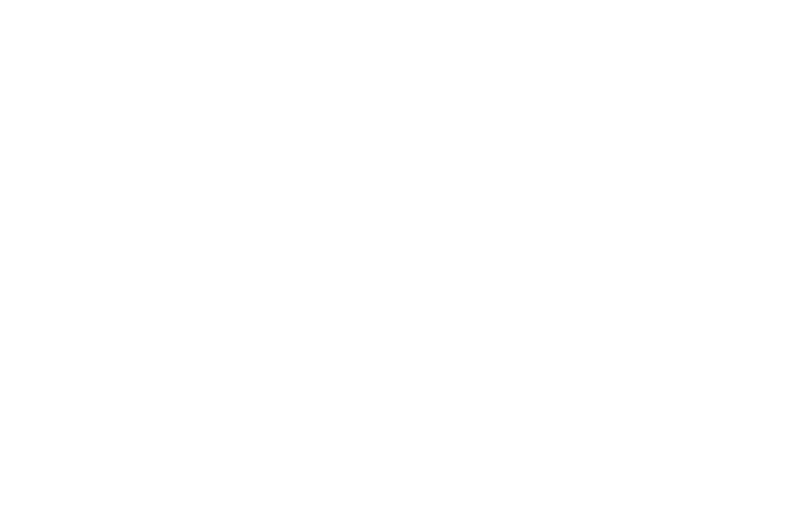在丹尼拉·梅斯特亚尼克·杨(Daniella Mestyanek Young)军训的第一天,她站在其他新兵中间,一只胳膊举着一个行李袋,高举过头顶。当她思考着在余光中排列的其他身体,都在努力保持同样的姿势时,她逐渐意识到这种感觉——被拥有、被胁迫、被编程——似乎令人不安地熟悉:“我是不是刚刚加入了另一个邪教?”
这种怀疑的感觉形成了梅斯特亚内克·杨(Mestyanek Young)生活的一种模式,她在回忆录《未培养的》(uncultural)中以非凡的洞察力记录了这种生活,探讨了毒性可以蓬勃发展的控制系统。
回顾:《un》——Daniella Mestyanek Young (Allen & Unwin)
Mestyanek Young出生在宗教邪教“上帝之子”,也被称为“家庭”。(不要和安妮·汉密尔顿·伯恩(Anne Hamilton Byrne)在澳大利亚的邪教组织(也被称为The Family)混淆。)
梅斯特亚尼克·杨(Mestyanek Young)的童年生活在巴西、墨西哥和美国的各个院落之间。15岁时,她逃离了她后来承认的邪教,来到德克萨斯州,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最终以毕业生代表的身份毕业,并加入了美国军队,在那里担任情报官员。
丹妮拉·梅斯特亚尼克·杨(Daniella Mestyanek Young)探索了有毒物质可以滋生的控制系统,先是在邪教内部,然后是美国军队。作者提供了
但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生存故事。这是一个exposé的虐待,可以在邪教中不受控制地运行。这是一个关于创伤的故事,是一本战争回忆录,是对文化和邪教之间差异的思考。这是对那些继续认为非男性服从于男性的群体的强烈控诉。
但《无教养》的核心是一本关于群体的书。它要求读者仔细观察在我们称之为自己的社区中运作的权力机制。
神的儿女
Mestyanek Young描述了她作为第三代邪教成员(“上帝之子的孩子的孩子”之一)的童年,细节令人心寒,但也有惊人的超然。
该邪教也被称为“家族”,因其广泛而系统的虐待而臭名昭著,尤其是对儿童的虐待。
该组织引用谚语“不打不成器”来为其剥削儿童的行为辩护。它让孩子们经常挨打,并要求他们永远可以满足邪教成年人的性冲动。Mestyanek Young出生时,她的父亲49岁;她的母亲只有15岁。
梅斯特亚内克·杨(Mestyanek young)从出生起就被编程,她就直觉地认为她的世界有些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年仅六岁的Mestyanek Young已经开始质疑《圣经》的合法性,他就被锁在一个房间里,被该邪教的一名成员,一位尊贵的叔叔反复强奸和殴打。
然而,尽管邪教采取了强制手段,Mestyanek Young还是能够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批判性视角观察它的内部运作,“尽管我是那个受到惩罚的人,但在内心深处,我怀疑错的不是我”。
阅读更多:宗教谎言,骗子和强制控制:邪教如何腐蚀我们对爱和联系的渴望
邪教的定义
《无文化》让读者重新思考他们对邪教产生和运作方式的看法。上帝之子很容易被定义为邪教。
它有一个领袖,大卫·勃兰特·伯格,当时的追随者认为他很有魅力。它有自己的说法:叛逃者是倒退者;等级制度中不可触及的成员是“细拉”。它将世界划分为道德的,内部成员和邪恶的,外部成员。它限制医疗保健,剥削其成员的劳动力。它的退出代价很高:不仅被驱逐出教会,而且被驱逐出稳定、舒适和使命感,这些支撑着围绕明确使命建立的生活。
“上帝之子”邪教及其领袖大卫·勃兰特·伯格(David Brandt Berg),当时的信徒认为他很有魅力。作者提供了
邪教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吸引了大量的学术关注,工作定义表明邪教是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使用类似的方法来吸引支持者,传播其意识形态,控制其成员,并将其世界观付诸实践。
但是Mestyanek Young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通过将她在《上帝之子》中所经历的强制和控制制度与她在军队中所经历的制度进行对比,她暗示了一系列广泛的制度在她对类似邪教行为的描述中。
对军队的崇拜
作为美国军队的一名新兵和军官,梅斯特亚内克·杨(Mestyanek Young)经常回忆起童年时期与她的军事经历相对应的例子。
她在任何地方都看到了相似之处:华丽的场面、无情的要求、吟诵、定制的语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在对上级的绝对忠诚,独特的学习资源,绝对的,持续的,详尽的成员期望。她还在同志情谊、归属感以及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追求明确目标的满足感中看到了相似之处。
尤其是,这本书迫使我们反思两个群体中男人的权利:例如,叔叔和船长,他们在为最坏的成员的可恶行为开脱的文化中工作。这两个群体的结构使男性能够以一种不仅被容忍而且被期待的方式接近下属的身体。
Mestyanek Young详细描述了男人的冲动是如何融入上帝之子和美国军队的权力结构的——在后者,尤其是当她被部署到海外时。
作为上帝之子的一员,Mestyanek Young被教导要“分享上帝的爱”,无论何时被提出要求,都要毫无疑问地从事性行为。在军队里,梅斯蒂亚尼克·杨发现自己和她的上级发生了性关系,这位上尉“在黑暗的掩护下,我根本没有感到有足够的力量说不”。
她被警告不要在部署时被强奸,同时被告知四分之一的女性将在部署时被强奸——被与她一起服役的男性强奸。
军队的强奸文化被诸如“强奸巷”这样的俗语所支撑;根据传说,女兵只能被归为三种类型之一:婊子、女同或荡妇。还有一种希望女性保护自己安全,但不希望男性不实施强奸的文化。
Mestyanek Young讲述了她在与上司的谈话中对工作场所强奸不屑一顾的过程,她的上司随口说道:
你知道,在我来到这里(阿富汗)之前,我曾经认为那些说自己害怕的女性只是在装腔作势。但我越习惯这里的情况,我就越觉得你在这里可能会被强奸。
一个退伍军人“熟悉的”视角
作为一名曾在澳大利亚军队服役的士兵,阅读这本回忆录时,我发现梅斯特亚尼克·杨(Mestyanek Young)对随意的性别歧视的详细描述非常熟悉。
当我还是一名现役军人时,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军队里没有女性,只有士兵”,意在表明一种平等:抹去女性性别,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包容性。
但这种类型的短语不仅仅是一个停止思考cliché掩盖谎言。这不仅仅是一个被选择性地、不公平地使用的短语。这是一种抹杀,错过了可以丰富组织的不同观点的见解和补充。
例如,在坎大哈巡逻时,Mestyanek Young喜欢看到孩子们——尤其是年轻女孩——在街上玩耍。在一次巡逻中,Mestyanek Young注意到周围没有这些女孩。这一观察结果挽救了她的巡逻队的生命:他们停下来,发现了一个爆炸装置,并中止了任务。
在去直升机的路上,巡逻指挥官说:“我喜欢你们在队里——你们会注意到最愚蠢的事情。”Mestyanek Young认为:
如果,我们如此不同,有着如此不同的生活经历,以及我们所注意到的所有愚蠢的小事情,就是全部意义呢?如果我们能拯救生命,仅仅因为我们是女人?
2010年,坎大哈市,一名美国士兵在一次信息收集行动中遇到了阿富汗女孩。斯蒂·维格斯沃斯/美联社
Mestyanek Young在这里提出了一些要点。首先,重要的是邪教内部的人——那些“好”成员——要挑战有毒的文化。组织内部随意的性别歧视和强奸文化会导致女性在代表国家执行任务时遭受独特的创伤,这些策略必须得到解决。
我们可以将Mestyanek Young关于多样性价值的观察延伸到无尽的群体环境中。但是很难从邪教内部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有毒的组织。
Mestyanek Young要求我们批判性地看待我们的机构,以及其中运作的文化和邪教行为。她恳求我们解开作为一个很难质疑其国防力量权威的社会成员所经历的程序。
阅读更多:周五的文章:为什么士兵犯下战争罪-以及我们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也许群体就是群体
关于邪教的文献和学术辩论并不缺乏。这本书做得特别好的地方是将我们对邪教的知识,通过暗示,覆盖到所有类型的团体。
《无文化》一书向读者展示了诱惑、胁迫和控制的方法,这些方法在邪教中非常有效,所以他们可能会在生活的其他领域发现它们。
她写道:
也许群体就是群体。邪教组织。伟大的军队。美好的家庭。神奇的国家。在上面堆任何你想要的修饰符。每种方法都有相同的固有优点、缺点和潜在缺陷。
这本书促使我们反思我们自己的群体——不仅仅是社会群体,还包括我们的工作场所、机构和政府——反思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以及我们在他们内部的关系。因为在一个环境中认识到有害的群体行为,我们就能在其他所有环境中对它免疫。
我们是在被要求去恨吗?观点的多样性是否被积极压制?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个小组上,和我花了多少时间在其他事情上?退出成本是什么?
学者们将继续争论邪教的准确定义。关于邪教和文化之间模糊界限的讨论将继续下去,也应该继续下去。但是,正如Mestyanek Young在这本书中所暗示的那样,也许精确的定义并不是真正的重点。也许,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识别可以在所有类型的群体中发展和恶化的控制系统。
Mestyanek Young关于组和编程策略的观察有很多应用。例如,我们当前的环境——算法化的新闻管理、日益两极化的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驱动的广播网络——将人们分为“在”和“不在”两个群体,这对邪教结构至关重要。
与unculture的论点相反,我们可以将这些策略理解为相当于编程:一种指导人们根据身份和群体思维(而不是推理和合作)做出决定的策略;一种长期以来一直是邪教惯用手法的编程方式。
在这个时代,极端主义组织通过互联网前所未有地接触到普通大众,甚至接触到商业领袖,比如埃隆·马斯克和亚当·诺伊曼,他们的行为被一些人描述为邪教般的行为,《无文化》是一本及时而迷人的读物。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