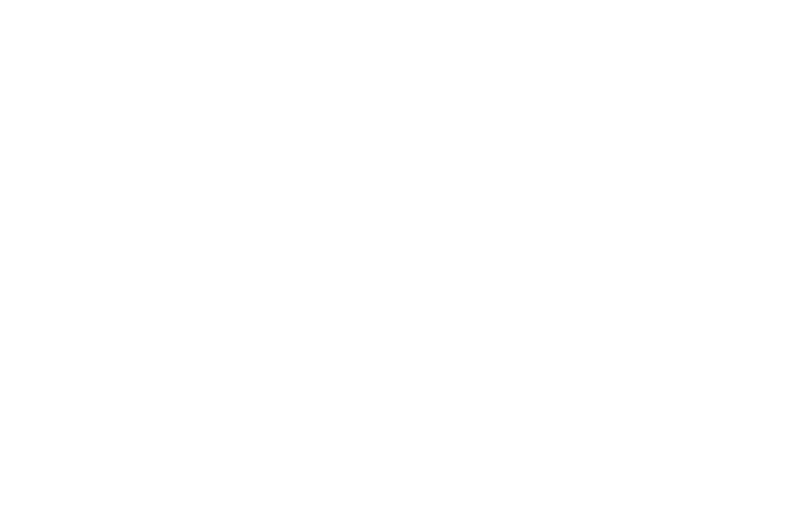摘自“粗糙的睡眠者:吉姆·奥康奈尔医生的紧急任务,为无家可归的人带来治愈”,作者是特雷西·基德67年。吉姆·奥康奈尔(Jim O 'Connell)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是那里的教授。1985年,他成为波士顿无家可归者卫生保健的创始医生。从那以后,他一直为《计划》工作,担任总裁和执业医生。当下面的故事发生时,他年近70,但仍然是“街头救护队”的队长,仍然在街头和他参与创建的周四街诊所为无家可归的病人看病。
吉姆曾经告诉我,他的工作有四分之三与社会工作有关,而不是医学。而且,他会说,并不是医学院培养了他,而是他为读完医学院而做的调酒师。“如果你不愿意听很多人对你说话,而且不是所有人都条理清晰,你在酒吧会疯掉的。”大多数街头小组的病人需要长时间的探访,有时是出于医疗原因,更多时候是为了精神支持。通常,在周四的诊所里,他会看5个,很少是6个,下午晚些时候就结束了。2016年9月的这个周四相对平静。正当他准备回家时,他的助手朱莉(Julie)从楼下的候诊室打来电话。一个新来的病人来了,要求看“吉姆医生”。朱莉说,这个男人看起来“相当狂野”。她告诉了吉姆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安东尼·科伦坡。1968年12月19日。
吉姆让她把那个人带到楼上的检查室。他满怀疑虑地做了这件事。他答应过他的妻子,他会在4点前回家,最迟是5点。也许他可以缩短这次拜访的时间——只会见这位新病人,安排改天再去看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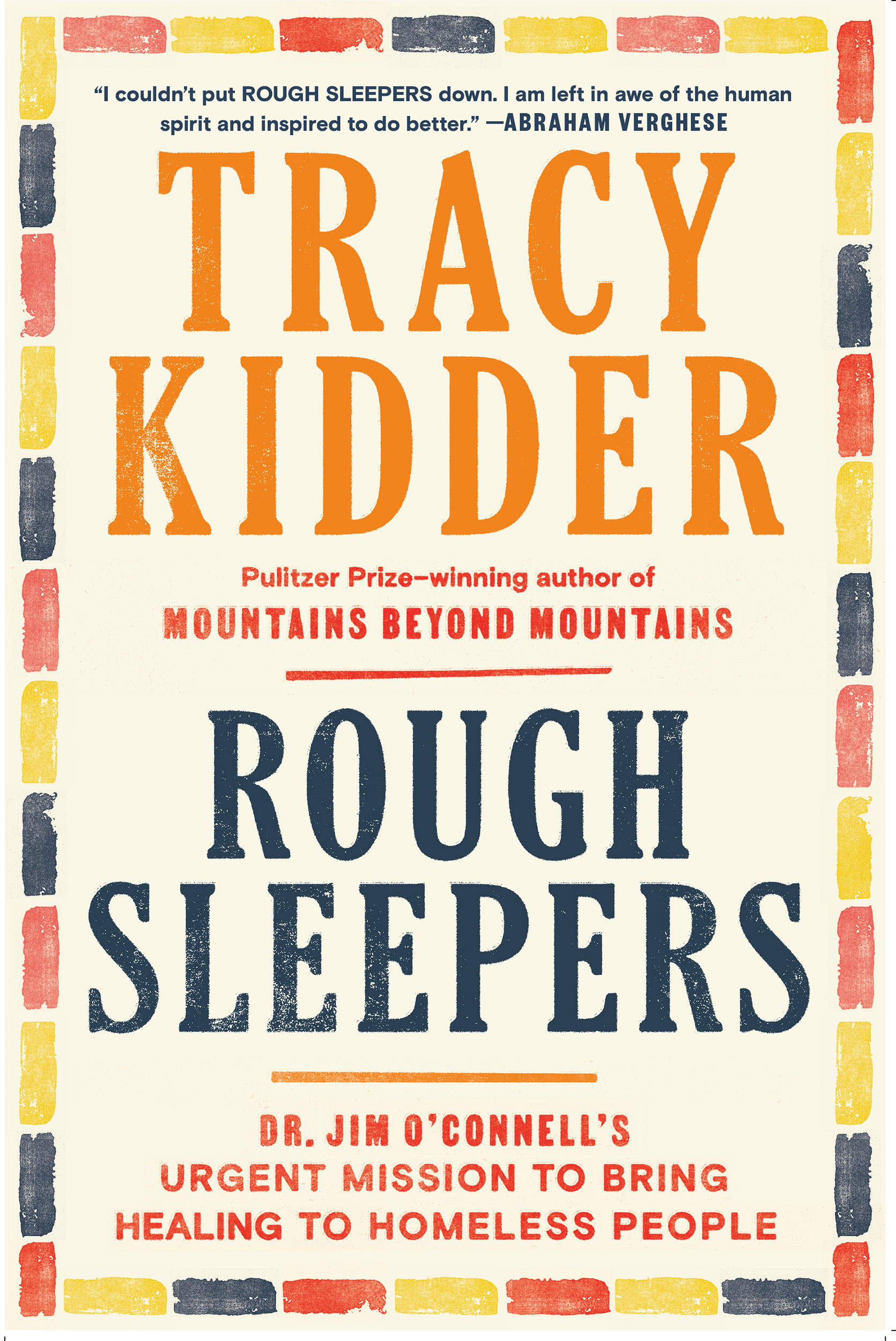
吉姆总是站着问候他的病人。他会对健谈的人露出倾听的微笑,同时仔细地观察他们。检查室比看门人的壁橱大不了多少,里面塞满了基本的医疗设备。当这位新病人走进来时,他把房间布置得更小了。他比吉姆高,高到吉姆不得不抬起头来与他的眼睛相遇。他介绍自己叫托尼。他有力地握手。即使当他坐在医生灰色金属桌子旁的椅子上时,他看起来也显得异常高大。他穿了好几层衬衫,但很明显,他身材精瘦,肌肉发达,看起来比大多数年近50的粗人要健康得多。他带来了一股汗味和微微腐烂的水果味。几天来长出的黑胡子烧焦了他的脸。他秃顶了,头发剪得很短,高高的额头上有几缕头发,他不时地用一团纸巾擦一擦——出汗要么是因为他的衣服,吉姆想,要么是因为服用了gaba - pententin,一种广泛用于引起狂喜的药物鸡尾酒的抗痉挛药物。这个男人的脸是典型的比例,有一个略微钩的罗马鼻子和深棕色的眼睛,在房间里观察地移动。
吉姆问托尼什么风把他吹来了。滔滔不绝的话涌了出来。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带有男中音的音色和波士顿口音的北端变体。
当他说“说来话长”时,他往往反其道而行之。他说,他在监狱里呆了20年,从那以后一直露宿街头,长期以来一直在监狱内外购买Suboxone毒品。吉姆经常开这种相当新的药来帮助病人戒掉海洛因。它本身只是轻度上瘾。托尼说他主要是用它来治疗背部和膝盖的疼痛,现在他因为戒药而感到不舒服——“Subo sick”。他现在需要一些苏波酮。
他用过其他毒品吗?吉姆问。
“我愿意,我愿意。”托尼说。“我抽很多K2之类的东西,有时也抽可卡因。”
在他的电脑上,吉姆找到了托尼的医疗记录,显示他偶尔在一个项目的诊所看到他,他被开了Suboxone来戒掉阿片类药物。
给他开处方是合理的,但吉姆不确定他是否应该这样做。托尼可能用苏波酮作为混合药物的基料。吉姆告诉他,他现在可以从他身上取尿样,然后下周给他一个剧本。
托尼眯起眼睛。效果是戏剧性的。它把他的脸变黑了,就像海上的北风。“嗯,事情就是这样。”他说。“这就是我不来这些地方的原因。”他在椅子上向前挪动了一下,准备站起来。
“等一下。”吉姆说。“坐一会儿。跟我说说。”
托尼坐了下来,告诉吉姆流落街头有多难,他现在有多痛苦。
这人的绝望是显而易见的。吉姆一边听着,一边转向电脑屏幕,又看了看托尼的病历。文件不多,但它证实了托尼所说的要点。吉姆想:“如果我现在不花时间给他吃药,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吉姆问,如果他给托尼开了一周的苏博康,他能保证下周四回来吗?
“该死的吧!托尼说。“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吉姆把剧本打了出来,交给了托尼。如果吉姆那时走,他到家只会晚一个小时。但是托尼说他还有另一个问题。“我现在没有身份证。”
吉姆的传呼机响了,打断了托尼的话。是吉姆的妻子。他打电话给她。他说他有病人在,能马上给她回电话吗?
“你该走了吗,医生?”托尼问。
事实上,吉姆说,他本该在4点钟离开的。“但是让我们完成这件事吧。”
他和托尼一起去了位于剑桥街的CVS药店,以证明托尼的身份。他们到的时候已经六点多了。药剂师接受了处方。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说托尼的医疗补助保险单出了问题。他们不会付钱的。
吉姆问药剂师这种药要多少钱。药剂师说120美元。
托尼爆发。“伙计!在街上?五块钱。”
吉姆掏出钱包,把信用卡放在柜台上。“用这个。”
“哇!不,不,医生。”托尼抓起名片,把它还给了吉姆。
然后药剂师看着吉姆。“等等,你就是那个医生?”让我再打个电话。”
最后一切都结束了。医疗补助最终还是会覆盖托尼的苏博酮。当他们离开商店时,吉姆问托尼有没有钱。他没有。他今天吃饭了吗?
“差不多。”托尼说。
吉姆回到屋里,从冷柜里买了一个三明治,然后把一张20美元的钞票塞进袋子里,递给托尼。托尼表示抗议。不是很卖力,但似乎是为了形式。
许多人不赞成这样的礼物,包括吉姆自己的街头团队的一些成员——不是三明治,而是现金。托尼会用这些钱买酒或毒品吗?
几年前,在一位曾经无家可归的病人和一位资深护士的帮助下,吉姆已经为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他要捐钱,他应该私下做,这样病人就有能力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他认为他们应该买的东西。几十年来,他一直遵循这个建议——起初每次给1美元,现在通常是10美元或20美元。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个项目给了他一笔可观的薪水,而他偷偷塞到病人手里的钱一年也就几千美元。
吉姆和托尼在7点多一点分手了,那个大块头沿着剑桥街摇摇晃晃地走了。吉姆后来告诉我,他给托尼的那20美元可能有治疗作用,这是他回来的另一个动机。
六个月后,托尼已经成为了街头医疗队的正式病人,也是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周四诊所的常客,通常由吉姆来看他。我在吉姆狭小的诊疗室里旁听了一次。
会议开始后不久,吉姆被叫走了,我和托尼单独呆了一会儿。他花时间称赞“吉姆博士”,称他为该计划的“小丑”。当吉姆再次出现时,托尼转向他说:“吹嘘你,说你创造了一支善良的军队。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你的事情,医生……”
“楼下简直是一场噩梦。”吉姆边说边在桌旁坐下。
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窃笑。听起来很勉强。
但托尼不打算让他改变话题。他继续表扬吉姆。华丽地。所有的街头小队都是“没有翅膀的天使”,但吉姆是“小丑”,是无家可归者的大天使。“一旦他们跌倒,他就会创建一支军队来接住他们。”
吉姆又试了一次。“你这么说真好。我希望这是真的。”
但托尼大声叫他闭嘴。“这是事实!”我是说,拜托!你没有歧视,你不只是对我,你是为所有人做的!”
波士顿医疗和慈善机构的一些成员曾向我描述吉姆为“圣人”,他们无一例外地谈到他的谦逊。事实上,吉姆把谦逊当作一种信条。他似乎本能地对赞美感到不适,尤其是对宣福礼。他曾引用他的前导师,一位名叫芭芭拉·麦金尼斯的护士的话,她曾告诉他:“这项工作太有趣了,不能被视为神圣。”但否认自己是圣人的问题在于,在许多人看来,这提高了你的资格。
我最初几次和托尼谈话时,他似乎非常容易分心。现在,当他继续赞美吉姆的时候,很明显,他会在一些问题上坚持不懈。
我不确定是什么激发了这种宣泄。住在街上的人容易接受每天经过他们身边的反对。托尼这种奢侈的赞扬在执行上似乎有点疯狂,但也许这是他先发制人的方式,以防止我们和他自己的反对——他冒着让医生不舒服的风险,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最后,吉姆放弃了抗议。然后转向桌面上方的电脑屏幕。他抬头看着托尼的病历。“告诉我你怎么样了。你的血压升高了一点,”吉姆像往常一样拉长了最后一个字,好像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在前一周托尼的预约中,吉姆以一种完全实事求是的语气说托尼的尿液中有大麻和可卡因。今天不一样了。“顺便说一下,你的尿液很好,”吉姆说,仍然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好工作”。他把血压袖带戴在托尼的胳膊上,说:“想点好的。”两小时前,托尼刚到楼下的候诊室,护士长量了一下他的血压,他的血压是172 / 101。现在,它已经降到了完美的水平,123比77。“托尼,你让我今天很开心。你让我今天很开心。”
“我让他高兴了,”托尼说。“听他说。他比我更担心我的健康。”
“医生关心你的健康。”吉姆说。“你在说什么?”
托尼又出发了,他说我应该随机找10个无家可归的人,问他们关于吉姆医生的事。“这些故事都是关于这个人如何富有同情心,如何关心他人。不仅仅是一个医生,也不仅仅是一个人。”
“现在你要给我一个大脑袋,”吉姆说。“但是你的尿液很好。我漏了什么?你还好吧——你的钱包拿回来了吗?”
托尼的办公室拜访有漫长的结局。街上的生活总是有正常的复杂性需要理清。托尼又一次丢失了所有的身份证件,这一次他的钱包在他睡觉时被偷了。每个月初,吉姆都会为他给病人的现金礼物做一个预算,他会带着5美元、10美元和20美元的钞票来街头诊所,这样他就可以不引人注目地递给他们。托尼很少要钱。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承诺会还钱。他还没有。但现在他又失去了一切,当吉姆递给他一张叠好的20美元时,他甚至没有假装争辩。
吉姆总是站着问候他的病人。他会对健谈的人露出倾听的微笑,同时仔细地观察他们。
他们一直在为他找公寓,似乎终于要有结果了。他每周都要补药,因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没有地方存放药物,必然会经常弄丢药。一位长期的病人曾经把药藏在内衣里。托尼在一些基本的事情上也需要帮助。病人们经常要餐券、出租车代金券和5美元的唐恩都乐(Dunkin’Donuts)等地方的礼品卡,这些地方既能提供食物,也能使用卫生间——吉姆的一个朋友称之为“拉屎的权利”。今天对托尼来说,是地铁通行证,这样他就可以去社会保障办公室办理新身份证了。“我讨厌偷偷上火车。当吉姆从他的医生背包里拿出通行证时,他解释道。
终于有了街上的消息,托尼可以告诉吉姆医生。“你听说约翰尼·史密斯死了。那个白发的?”
“什么?吉姆说。“哦,人。我没听说过。”长时间的沉默。
然后他对托尼说:“你就像我在外面的眼睛和耳朵。”
“我很喜欢这次访问,”托尼说,六英尺四英寸的他站了起来。
后来吉姆在他的办公桌前逗留了一会儿。他笑了。“朱莉和我总是要花10分钟才能从托尼身上恢复过来。”
在吉姆的记忆中,有一个多年前生动而神秘的病人的万神殿。两位前大学教授脱颖而出。哈里森和大卫。两人都受到精神疾病的折磨,其中大卫最为突出,也最为奇怪。精神病学家所说的固定妄想扭曲了他的生活。他相信他在佛蒙特州生下了一个双头孩子,而他仍然因此受到那些装备着他所谓的“zappers”的人的追捕。无论精神病医生、吉姆还是一位前来尝试的教授朋友,都无法说服他放弃他那奇异的幻想。然而,在流落街头的同时,大卫成为了教堂唱诗班及其社会事工的一员,在公共图书馆辅导各种各样的人。他曾顽强地去监狱看望过一个黑人青年,并帮助他获得了自由。
至于年长的教授哈里森,他说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获得终身教职的最年轻的人,他还是杰克·凯鲁亚克和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等人的朋友。吉姆找到了大量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真的。当吉姆告诉哈里森他喜欢凯鲁亚克的书《在路上》时,这位老教授说:“杰克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但却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思想家。”
吉姆以前每个月都带哈里森和大卫去联合牡蛎馆吃一次午餐。他会倾听他们争论哲学和文学问题——后现代主义真的存在吗?年长的哈里森会笨手笨脚地把蛤蜊浓汤洒在自己身上,吉姆会坐在那里觉得有点恶心。现在他会说,他对自己的神经质深感后悔,他觉得和那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很珍贵。哈里森是几年前去世的,大卫是最近才去世的,都是自然死亡,而且对于露宿街头的人来说,也就是“露宿街头的人”来说,已经是高龄了。
托尼被冲到街头小队的岸上已经快一年了,他的活力似乎已经成为吉姆的先贤祠的候选人。“我觉得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大卫了,哈里森去世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吉姆告诉我。“我没想到会有新的角色,所以托尼是一个惊喜。他是不同的。哈里森和大卫站在与其他病人分开的地方。并不是说他们冷漠,而是说他们不属于这些露宿者的群体。托尼就在漩涡的中心。他出狱后似乎认识街上的每个人。”
在检查室里,吉姆等着他的下一个病人,最后对托尼说了几句话。“他有密码。他有点像个打手。如果你不伤害别人,你就没事,但如果你伤害了别人,你就不行了。”
渐渐地,房间本身似乎平静下来了——仿佛它也有了脉搏,恢复了正常。现在托尼身上只剩下几根羽毛,从他大衣上的洞里,还有办公室浅绿色油毡地板上的白色绒毛。
版权所有©2023 by John Tracy Kidder。由兰登书屋出版,企鹅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的印记和部门。版权所有。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