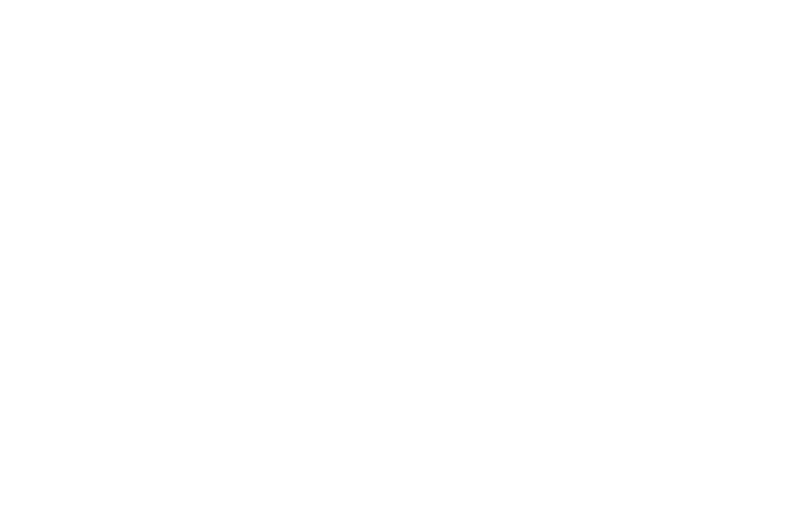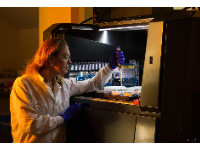“我认为护理不受重视,因为这是女性的工作。 女性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会贬值。”
从出生到死亡,每个人都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接受过护理。 而“照料经济”就是提供托儿、养老、医疗等照料服务而产生的经济活动。 这包括有偿和无偿工作,可能涉及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等一系列部门和行业。
但我们如何重视这种至关重要的护理呢? 谁决定某人的护理为经济增加的价值? 为什么如此多的护理被视为“女性的工作”并因此贬值? 这些问题是三一艺术与科学学院几位教职员工近期奖学金的核心。
什么护理很重要
“人们在思考护理经济时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衡量它?’”乔斯林·奥尔科特说。 作为历史、性别、性与女权主义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的教授,奥尔科特说有两种不同的护理:一种是“算”为市场一部分的护理,另一种是不属于市场的护理。
“全食超市的付费护理、付费儿童保育或热吧都算作 GDP 的一部分。”她说。 GDP 代表国内生产总值,即一个国家境内生产的所有商品和服务的货币或市场价值。
“但如果你回家照顾自己的孩子,尽管这感觉像是工作,但它不会增加 GDP。 实际的劳动、时间、专业知识和注意力,以及所有我们认为在这些其他领域工作的东西,如果不进入市场,就不算工作。”
谁在从事大部分无偿劳动? 女性。 奥尔科特说,性别分工一直存在。
“当我们想到护理经济的主要部分时,它们绝大多数是由女性驱动的,而且在大多数行业中,都是有色人种女性。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情况下,这些护理工作监管不力,工作条件和工资都很差,而且由少数民族和种族边缘化的女性担任。”
根据奥尔科特的说法,市场护理(可以衡量并给出价格标签)和非市场护理(包括所有形式的免费护理劳动力)之间的护理划分是 19 世纪的产物。
“它主要伴随着对工业化的大力推动和资本主义的创造。”她说。 她指出,这一切都与 1940 年代 GDP 的诞生和采用有关,关于什么构成经济以及什么构成该经济中的生产性工作的对话。
“许多研究护理经济的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衡量护理的所有方面,它就会保持隐形。”奥尔科特说。
奥尔科特注意到,今天的学生比过去更了解护理经济的动态,以及平衡职业和家庭的意义。
“但许多人仍然坚持这样一种误解,即如果有偿护理,就不可能是真实的。”她指出。 “如果他们有保姆或把孩子送到日托所,他们得到的感情和爱就不是‘真实的’。”
她认为这种误解——护理的贬值——与护理劳动的报酬过低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她目前的研究挑战了这个想法。
奥尔科特正在开展一个名为“全球经济中的护理重估”的跨学科项目,该项目通过一系列讲座、艺术展览和会议揭示了当今护理的现实。 该项目的核心是一个具有开放访问书目的网站,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输入与护理相关的关键字并查找文章和书籍以帮助他们进行研究。
“我们真的在努力创造资源,使之成为可能,特别是对于教师和记者来说,获取有关护理和护理经济的信息。”奥尔科特说。
“他们是变革的驱动力。”
被低估但拯救生命:分娩和产后护理
从字面上看,对护理经济的依赖始于出生。
詹妮弗纳什关于黑人母性的奖学金涵盖孕期护理、分娩和产后护理。 虽然她的工作重点是黑人母亲面临的具体挑战,但她的发现超越了种族分歧。
在她最近的一本书“分娩黑人母亲”中,纳什采访了与孕妇和产后妇女打交道的人,从医生到助产士再到导乐——在分娩期间提供协助的非医疗分娩工作者。 她向她们询问女性在生完孩子后的第一年需要什么,以及这种形式的护理工作如何降低持续不断且令人担忧的黑人孕产妇死亡率。
纳什发现她为她的书采访的助产士不仅通过帮助他们照顾家里的新生儿来支持家庭,而且还通过将他们插入重要的支持网络。 他们知道哪些哺乳顾问是最好的; 他们知道儿科医生支持什么; 他们联系了同时有孩子的客户。
“隔离在美国尤其是产后生活的一部分。”纳什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假期很少,而且很多人与家人和朋友住得很远。”
“现在对于产后需要什么样的护理有更广泛的概念。 但我发现,这种广泛的护理概念并不是由医院或国家推动的,而是由像导乐这样的人推动的。”
纳什说,导乐还可以帮助那些可能不信任医疗机构的女性。
“人们会告诉你一个关于去看医生的故事,感觉他们必须说服医生,或者他们必须为自己辩护,或者他们不被相信,这已经成为我们接受的关于医学的普遍故事。 ”
纳什指出,与她交谈过的大多数非医疗助产士并不是仅靠护理工作的工资维持生计。
“这些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非常重要,以至于他们在 Target 或幼儿园工作之外还这样做。”Nash 说。 “然后,毕竟,他们养育了自己的孩子。 作为导乐工作,这甚至不是第二班。 这就像第三次、第四次或第五次轮班。”
纳什指出,从事生育工作的女性并不是唯一被低估和低薪的女性。 这个问题延伸到儿童保育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美国并不认为日托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她说。 “这些又是有色人种女性从事低薪工作,照顾孩子并保证他们的安全,她们的劳动保障了职业母亲的自由。”
没有人愿意考虑的护理:疾病和老年护理
在美国,作为工作父母驾驭儿童保育的复杂性并不是秘密——并且因 COVID-19 大流行而加剧。 然而,很少有人了解照顾生病或年老亲属的复杂性。
尽管老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老年护理并没有像儿童保育改革那样受到关注。 Gilhuly Family 历史学副教授 James Chappel 的研究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
他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转变之一是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以及 65 岁以上的人口占多数。与此同时,成年子女仍与父母同住或住在附近的情况非常普遍 二战前,分享收入和责任。
“这更容易,因为人们的寿命没有那么长。 如果有人死于 67 岁,那与死于 87 岁的人有很大不同。”Chappel 说。
人口动态的转变塑造了我们的社会关心谁以及如何关心。 “过去有很多孩子,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死去,而且没有那么多老人。”他说。 “护理工作真正关注的是儿童以及如何让他们活得更久; 在美国,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由于医学和技术的进步,老年人的寿命也更长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你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老年人应该独立——他们应该打网球并拥有充实的社交生活。”Chappel 说。
他解释说,这种对老年人独立性的新投资导致了退休社区、有年龄限制的私人社区和老年人俱乐部的出现。 但立法和政策未能满足大量老龄化人口的巨大需求。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有很多老年人的社会中。”Chappel 说,“老年人护理特别需要在美国政策网络中占据更大的比重。”
对话没有跟上动态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女性是主要管理和执行老年护理的人。
“中年女性不得不免费做这件事。”Chappel 说。 “女性通常负责照顾老人的日常工作,从开车送人到约会,让年迈的父母搬进来与她们同住,再到在行动不便时帮助她们活动身体。”
女性不仅负责日常护理,她们还在开发她们在其中工作的基础设施。 很多人想到这一点都会感到不舒服。”
他说,许多人害怕需要帮助,无论是来自家庭还是社会服务,人们可能很难适应需要改变父母关系中的权力动态。
“照顾孩子在很多方面都是有益的。”Chappel 说。 “你让他们更加独立; 你正在创造未来的公民。 照顾老年人并非如此,而且在某些方面更具挑战性。 对于某些人来说,当然,这是非常有益的。 但对许多其他人来说,这在情感上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正在处理一个衰落的故事,而不是一个成长的故事。”
在最糟糕的时候寻找快乐:生命的终结和悲伤护理
关怀不会随着死亡而结束。 那些在亲人去世后留下的人不得不面对堆积如山的官僚主义以及他们的悲痛。 虽然有人可以参加产前课程为分娩做准备,但临终关怀和死亡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讨论的。 照顾临终者乍一看可能令人沮丧,但这种重要的关怀行为可以带来快乐并带来成长。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的个人主义文化和对进步的强调,我们很少谈论死亡。”斯拉夫语言和文学副教授兼健康人文实验室联合主任 Jehanne Gheith 说。 “我们也倾向于把死亡和死亡的想法赶走。 拒绝对很多事情来说都是很好的。 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否认只意味着我们没有工具去面对损失。”
盖思 (Gheith) 的职业道路与众不同。 她是一位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文化的学者,杜克大学斯拉夫系主任,并以悲伤顾问的身份经营着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在她哥哥于 2003 年突然去世后,盖斯对生活的不确定性以及如何最好地度过她在地球上的剩余时间进行了广泛的反思。 她决定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学位,专攻临终关怀和悲伤。 她的目标是支持濒临死亡的人及其家人,引导他们度过临终过程并帮助他们处理悲痛。
但这看起来像什么?
“在美国,我们在临终关怀中所做的两件事是临终关怀和姑息治疗(也适用于未患绝症的人)。”Gheith 说。 “临终关怀社会工作者进来并提供情感支持和资源,例如将患有痴呆症的人带到成人日托或帮助他们管理它。 在得到绝症诊断后,人们立即陷入危机。 那是第一次考虑这些事情的可怕时刻。”
她还强调,通常需要为临终关怀承担无形负担的女性提供支持。 他们的角色可能会从第一个注意到父亲的记忆出现问题的人,到进行预约,再到主动将看护人带回家。
“这个领域的许多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她们过度紧张。”盖思说。 “当你在工作和照顾他人时,很难抽出时间,甚至很难想象你可能需要时间独处。”
“我希望这种社会对话有所不同。 我希望人们谈论死亡和悲伤的过程有多么艰难,以及如何在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时获得天赋。 但知道何时寻求帮助也很重要。”
Gheith 对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医疗专业人员说了同样的话。 在 Duke Hospice 担任临终关怀社会工作者以及在 Duke Hospice Bereavement Services 担任丧亲辅导员期间,Gheith 一直在想方设法帮助那些经常处理如此多死亡事件的医疗专业人员。
“博士。 安东尼·加拉诺斯 (Anthony Galanos) 是杜克大学的一名姑息治疗医生,他针对工作场所的悲伤制定了很多规程,”盖思说。 “似乎有帮助的一件事是留出时间,护士们可以聚在一起说,‘是的,这周病房里有五人死亡,这真的很难。’”
“这个领域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的诱惑。 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短期策略,但它会导致长期的倦怠。 花一些时间承认悲伤往往会帮助人们更快地融入它。”
Gheith 认为最有助于减轻护理负担的事情是什么? 探亲假。
“我们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探亲假政策,”她说。 “我们需要能够为生命的各个阶段提供支持。”
尽管工作可能具有挑战性,但 Gheith 从中找到了很多乐趣。
“人们认为这总是令人沮丧——而且确实如此。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生命的尽头有很多欢笑。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