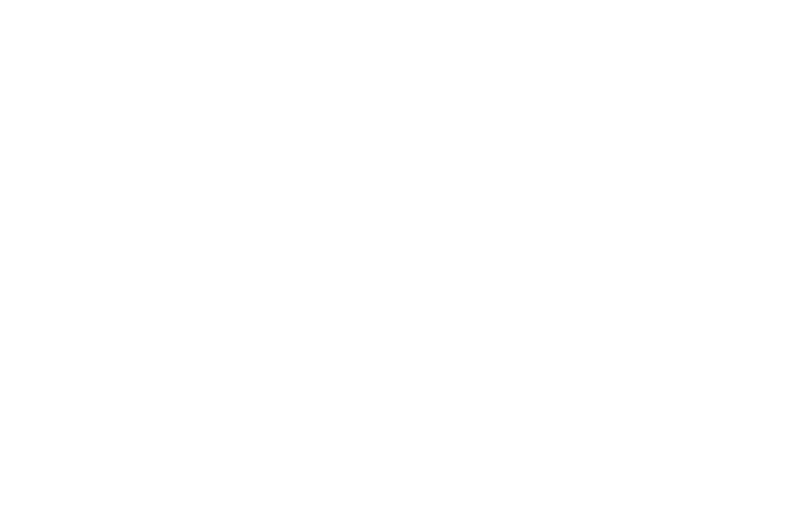1985年的夏天,中世纪的意大利小镇古比奥(Gubbio)周围充满了压抑。树木繁茂的峡谷和无风的山坡上,人们爬过翁布里亚,一直爬到亚平宁山脉的山麓。在小镇后面的山上,一小段蜿蜒的车程就是Libera Università di Alcatraz,这是一个僻静的隐居之地,正在成为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的聚集地——一个他们可以逃离大自然并进行创作的地方。
在意大利,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运转。建筑还未完工。游泳池的水已经排干,所以可以在池底画一幅龙的壁画。但不知怎的,这个地方很好用。客人在白天与他们的缪斯交谈,然后聚集在露台上吃饭,在安静,温暖的晚上,享受由当地食材准备的乡村美食,喝红酒,从聚集的创意人员那里听到故事。
这家企业由30岁的雅格布·佛(Jacopo Fo)经营,他涉足企业的各个方面,包括游泳池里的龙。在艺术品完成之前,游泳池不能被填满,以让客人们在无情的夏日炎热中得到一些喘息。
在尘雾和空中飞舞的萤火虫中,一场不可思议的聚会正在发生。雅格布的父母来了,达里奥·弗和弗兰卡·拉姆。他们在雅格布的领地扎营排练一部新剧。
Fo和Rame是意大利的文化贵族。距离演员兼剧作家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12年的时间,但他已经被公认为国宝级人物。他在艺术喜剧方面的开创性工作颠覆了戏剧的本质。他的戏剧将人物塑造成直接向观众讲话的怪诞人物。他们的无法无天的旁白是对古典戏剧对英雄主角的拥抱的攻击。
佛的新剧《伊丽莎白:一个偶然的女人》将由芬兰的一家戏剧公司演出。该剧将于几周后在著名的坦佩雷戏剧节上首演。
这出戏不完整。
佛不会说芬兰语。
芬兰人不讲意大利语。
一名翻译被雇来理解Fo对演员的指示,以及每天发生的许多重写。她的名字叫Aira pohjanvara - buffa。因为她要在翁布里亚的森林里露营一个月左右,她邀请了她的新伙伴。他是一位受人尊敬但鲜为人知的英国小说家,名叫巴里·昂斯沃斯。
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昂斯沃斯的历史小说吸引了一小群热情的读者。七年后,他将凭借《神圣的饥饿》(Sacred Hunger)赢得布克奖,这部小说以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恐怖为背景。
因此,从1985年6月下旬到7月中旬,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位未来的布克奖得主共同生活在翁布里亚森林的和平和田园般的宁静中。
排练彻底失败了。
第一天,演员们醉醺醺地从机场赶到。排练场还没建好。佛每天、每小时都在修改剧本——通常是在演员们等待新台词的时候。芬兰人的传统方法与佛和拉姆的无政府主义方法之间存在冲突。主角中暑病倒了。导演带来了他年轻的男朋友,这个年轻的男人开始对剧团的一些年轻女人感兴趣。在无情的高温下,人的脾气会变得暴躁。
与此同时,昂斯沃斯一直写着一本细致入微的日记,记录了神秘的佛的艺术方法,以及这部似乎注定要走向灾难的作品的幕后混乱。
几十年来,这本日记被遗忘了。它被捆在作者的论文和信件中,最终在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哈里·兰森中心的档案中找到了归宿。日记在昂斯沃思论文的12号盒6号文件夹里。它的观察是用清晰的草书写的,似乎是蓝色的圆珠笔,偶尔有红色的注释。
它有时会让人读起来很残忍。
这本杂志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这位20世纪戏剧雄狮之一的创作过程,以及其混乱的辉煌。虽然它是一个简单的线性事件的叙述,昂斯沃斯设法写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叙述,并创造了完全真实的人物。
巨大的希望
就像所有这类创造性的冒险一样,它始于巨大的希望。
6月20日——从罗马驱车前往利比里亚Università di Alcatraz,它距离古比奥只有几公里,距离佩鲁贾也不远。翁布里亚温和的绿色山丘,后面是亚平宁山脉较暗较高的山坡。有城墙的山顶城镇。近山的规模小到可以管理,但非常陡峭的峡谷,通常树木茂密。恶魔岛本身(靠近圣克里斯汀娜村庄)坐落在海拔6000米的绿色丘陵地区。
但昂斯沃斯很快就意识到,未来企业的基础存在一些脆弱性。
在罗马会面的芬兰公司中,有一个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另一个则有点醉。他们在飞机上一直在喝酒[…]他们俩都继续不停地喝,但那个五官很紧的那个还差点儿醉,而那个金发的——我想是更敏感的那个——到了晚上就醉得无可救药,几乎说不出话来。
Willi是公司的董事(他们来自距赫尔辛基约200英里的坦佩雷),对此一直感到担忧。如果他们得不到严厉的处理,他们很可能会陷入酗酒的模式,这可能会使他们不适合工作,并严重影响戏剧的进行。
即使在他的日记中,昂斯沃斯似乎也不反对做一些戏剧性的铺垫。这位未来的布克奖得主对佛的传奇很好奇,他的神话是否与现实相符。他对身体和心理的描述都是法医鉴定。
佛本人并没有接管这出戏的导演,因为他的医生告诉他要小心行事。他每天会练一小时,他现在是这么说的——以后的热情和投入还有待观察。
他个子很高——我想至少有六英尺高——胖乎乎的,穿着很随便,但尽管如此,他的身材还是很有气势的,有一种自然的尊严和从容的态度。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几乎是总督——几乎是罗马元老院——的特征,大脸,肉肉,大鼻子略尖,但这种印象很快就消失了。如果他的脸能平静下来,笑容能消失——这两个条件从未实现。这张脸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有一种优雅的严肃,一种几乎经常交替的模糊的抽象和温柔的精明和机警。
在良好的幽默感下,他保持着坚定的态度,对工作全身心的投入。他的眼睛很亮蓝色,脸色红润我想通过他最近的疾病。与舞台上令人惊叹的曲目和流畅的动作、姿势和手势相比,在谈话中,他仍然,一点也不太表露(因为他是意大利人)。
昂斯沃斯在这本日记中多次重温了福的性格中令人费解的本质。公平地说,作者一开始是好奇的,然后是钦佩,最后是极大的失望,因为这个人不等于他所创作的艺术。佛的饰面和任何舞台布景一样薄,目的大致相同:画出一幅图像,让观众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宏伟事物,但它本身是一种模拟,一种构造。
我参观了佛在光秃秃的山坡上建造的舞台,在斜坡的顶部,在通往塔楼的尘土飞扬的道路下面,左边的楼梯通向一扇门——伊丽莎白的房间。背景是一个拱形的栏杆,我想下面有一个狭窄的圆形平台。六个相同的拱门形成了一个拱廊的效果[…]不是一个出口或入口的方式,而是给人一种宫殿内部的错觉。右边中间是一个有窗帘的房间。有轮子的真人大小的马。(这是临时的-但需要用于商业生产。)
这一套在全剧中没有变化。我站在那里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移木板,清扫舞台区域的灰尘和杂物。工人们拿着梯子,手推车,支架,水桶。
这项工作将在明天或后天完成,为与芬兰人的排练做好准备。还没有完成,但它已经是一个内部——一个围栏(木板墙把它从岩石上划开,四周都是擦洗),一个可以让有因果关系或后果的重要事情发生、呈现的地方。
当一位艺术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另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时,通常是通过他们自己的作品来看待。以昂斯沃斯为例,他被佛的舞台艺术所吸引。
6月21日——这一天的开始是达里奥对戏剧的总体态度的谈话,然后是他对这部特殊戏剧的意图。他谈到了所谓的“古典戏剧”,这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因为它不考虑日常生活,也剥夺了演员的独立性。
他将其与艺术喜剧进行对比,从中他得出了自己的模型:固定的角色可以代表社会的不同方面,冲突中的不同论坛等等。谈到了在这个流行的剧院里即兴的品质,使得像donnazza和傻瓜这样的角色能够评论行动,支持怪诞或破坏价值或显示“英雄人物”虚伪立场的真实本质,也允许这些相同的角色在一旁讲话或直接与观众交谈,从而使他们更紧密地参与进来。
佛强调个人内在的尊严,强调权力和操纵以及国家的目的。解释在这部戏剧“伊丽莎白”中,他试图遵守15世纪意大利戏剧家的规则和基本形式——地点、时间、繁体字的使用等,以阐明隐藏在陈词滥调和被视为历史的虔诚之下的真相。
该剧以伊丽莎白一世的宫廷为背景,贞女女王对莎士比亚讽刺她统治的戏剧感到愤怒,并哀叹她的爱人埃塞克斯伯爵正在密谋反对她。和佛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是一部关于权力滥用的专著。他的职业生涯建立在对独裁政权的严厉讽刺之上,作品包括《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1970)和《付不起钱吗?》不会支付!(1974年),这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认为是贫困工人的捍卫者。
1962年,达里奥·福和弗兰卡·拉姆带着他们的儿子雅格布。维基共享
阅读更多:经典指南: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喜剧
上帝主题
那天晚上吃饭时,两个喝得酩酊大醉的演员向佛道歉,佛警告他们如果再犯,后果自负。该剧导演阿图罗·科索来了:
一个瘦削的、不安分的男人,一张瘦削的、奇怪地像鸟一样的脸,像鸟还是像哺乳动物?突出的鼻子,大眼睛,下巴向后缩。聪明的眼睛,随时准备微笑,我想他习惯了自我表达。
刚来的还有Corso的年轻男友Alfredo:
非常漂亮——她的五官大胆而匀称,意大利年轻人的眼睛既深邃又肤浅。吃饭时,弗兰卡问他(科索)阿尔弗雷多睡在哪里。他说:“当然和我一起。”他在提到阿尔弗雷多时使用了女性代词。
昂斯沃斯对佛的观察和他的方法几乎立即开始调整。他在6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彩排开始时,芬兰人将面临一个严厉的监工:
早上露台上很冷,没有阳光,但达里奥已经下定决心要在那里排练。他在这类事情上独断专行,粗心大意。
现在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女性的特质,一种崩溃的潜力[…]与那里的权威气质形成对比。他的这两张脸似乎象征着他戏剧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权力的冲突,对权威的维护和同时的破坏。
他对声音和表情有着惊人的控制能力,因此在插图中,他可以大笑大笑,愤怒尖叫,眼睛不会因为意图的严肃性而改变——他立即恢复到排练的正常语气,没有停顿。
很快,昂斯沃斯在他对佛的工作和玩耍的观察中确定了一个上帝的主题。他指出,表演中的人物通过他们的行动和思想质疑上帝的话。佛不断地编辑和重写他的剧本,甚至在阅读的过程中,被总结为:“上帝改变了规则?”
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弗雷多透露自己只有16岁。这促使Unsworth在期刊上观察到:
(芬兰人喝酒的时候,意大利人在尝试诱惑。)作家/演员就像上帝,因为他让实际的身体运动起来。
第二天,一个热水瓶被拿来给Franca Rame,她在早上紧张的排练后晕倒了。
佛穿着旧t恤和裤子,胖胖的,慈祥的,奇怪地漫不经心地穿过这一切。上帝和他的创造物一起放松,但仍然不是他们。
在漫长的排练过程中,昂斯沃斯偶尔会离开剧团,在周围的山上漫步,那里开满了金雀花、野甜豌豆、罂粟和矢车菊。正是在这些逗留期间,他开始为一部可能的小说做笔记,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一位国际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他买下了一块相当大的土地,在荒野中建造了一座剧院:
一个长长的露台(温室),回忆室,排练室,一个大餐厅。游泳池。他把古老的建筑、谷仓、塔楼——中世纪的建筑——改造成住处。这个地方很美——这是伊甸园,他是上帝。(有瑕疵的上帝?)他的配偶是他的女演员妻子。
这位副导演是基督人物。一个剧团的演员来排练一个新剧。这是一部中世纪道德剧,一部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还是一部外国戏剧?是剧作家写的还是改编的?它应该是a)对剧作家本质的评论;权威(这可以通过指向性评论来实现),关于政治权力的性质与当今英国的参照,以及其中的关系。
十年后,昂斯沃斯的小说《道德剧》入围布克奖,这部小说讲述了14世纪英格兰一个旅行剧团的故事。
达里奥·福在古比奥,1988年。维基共享资源CC BY-NC-SA
日益紧张的
到6月24日,公司内部日益紧张的局势变得明显起来。佛不断修改剧本,又不愿让科索全权担任导演,这给演员们带来了压力。福和拉姆决定离开几天,让科索负责。
大自我对疲惫的反应是寻求为自己简化,随之而来的是混乱。
达里奥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这里,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他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晒日光浴。当他脱下衬衫时——他是在一段距离内脱掉的——他的胸部明显下垂,甚至相当丰满,这证实了他在身体上是女性化的。(尽管他也有强烈的男性形象。)
难道他不愿意做日光浴就是因为这个吗?我们的神是徒然的吗。
尽管昂斯沃斯对佛的气质和实质有所保留,但他对他的舞台技巧毫不掩饰地钦佩。他描述了Fo向扮演Donnazza角色的演员展示如何移动:
他演示Donnazza的滑倒——向后看,后裙的荷叶边,向后弯曲的身体,然后是跳跃和滑行,发现尿——接受有一匹木马会尿——这些都是绝对娴熟的——每次他都一样有趣(每次大家都笑)。作为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在舞台上的动作轻盈而优雅,就像一个舞蹈家,他的动作精准而有节奏。(显然,舞台的空间和舞台上的主题对他来说是可以商量的,就像熟悉的客厅一样。)
在神的国度里,从上头来的一句话,是很有分量的。6月25日,昂斯沃斯写道:
达里奥告诉我,我有一张“聪明的脸”——una facia intelligente。在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下,他所有的赞美和评论都有某种约束力,在事情上盖章——甚至创造了他选择评论的事实。
然而,昂斯沃斯不会轻易被赞美之词欺骗。他的作品充斥着对撒切尔时代新自由主义的主题批评,以及撒切尔政府的政策对他的家乡英格兰北部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他有着北方人对夸夸其谈和自命不凡的不屑,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昂斯沃斯认为佛的日常举止和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一样具有表演性
一个人会被表演元素所压抑。因为达里奥是事物的中心,快乐的主人,朝圣的对象,作者和榜样,有时他似乎是在为我们调解生活。昨晚我们都被叫去欣赏日落,这是在吃饭的时候。我拒绝了一段时间的集体邀请,但或多或少还是被a拉了出来。这的确是一次美丽的日落——光彩照人,玫瑰色的,西边低垂的云镶着亮金色的镶边,高处的云卷曲着,在天空中抛洒出巨大的光晕。正如达里奥所描述的“拉斐尔式”。他为这个地方,为他所创造的东西感到自豪,这包括日落,也许还有整个翁布里亚。尽管如此,这种(对我来说)压迫感仍然存在。
与此同时,演员们也越来越厌倦他们队伍中这个难以相处的宙斯般的人物。
达里奥是一个徘徊的存在,现在芬兰人相当害怕,因为他不可避免地习惯改变文本(因为他有时不能完全记住它,也因为他没有耐心去理解芬兰人在文体上的困难)。如果他们不能立即明白他的意思,他就会变得不耐烦。我想当他和弗兰卡离开的时候(明天?)
但即使Fo和Rame离开几天,排练也会遇到麻烦。来自芬兰的到期付款没有出现。表演者又开始喝酒。扮演Donnazza的演员因中暑而病倒,其中一名芬兰人必须回家参加父亲的葬礼。导演科索在一次富有表现力的手挥时,不小心用锋利的指甲盖划破了自己的眼皮,他必须在脸上缠着宽大的绷带进行排练。Fo和Rame回到这个不稳定的领域,只是为了增加工作量。
现在早上开始排练。不管这些人多么热心肠,他们的优先事项很少考虑别人的感受。如果他们再次开始修改文本,被逼无奈的芬兰人可能最终会造反。
Fo和Rame背后的创作力量似乎是对现状无休止的不满。不断的调整,不断的改变。
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弗兰卡立即开始修改独白的文本,引起芬兰人的无声愤怒。这似乎是一个不由自主的过程,就像呼吸一样自然,达里奥和弗兰卡。问题是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偏好。
无论如何,观看弗兰卡为芬兰人排练是一种相当令人惊叹的景象。从她踏上舞台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在演戏。她扮演导演的角色。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研究了,走路的姿势,身体和头部的姿势,等待她的话被翻译时的倦怠,精心准备的耐心,突然转变为说明的动作,几乎令人麻木的权威的压低声音,对谈话的无情控制。
达里奥的风格不同。他总是出现在舞台上,以他轻盈但肥胖的姿态移动,偶尔会突然表演出令人惊叹的哑剧、语法剧或某种舞台表演。阿图罗坐着观看,站起来,上前用他高超的手势解释和说明(il maesto dilgesto),然后又回到他的座位上观看。
几周以来,排练一直在拖延。但随着电影节日期的临近,也有了一些进展:演员们开始完全融入他们的角色;剧本已经完成。表演快准备好了,昂斯沃斯该出场了。
最终,作者在艺术家和普通人之间左右为难。在大师面前待了一个月后,昂斯沃斯带着一部新小说的暗示离开翁布里亚,这是20世纪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之一的创作过程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他1985年8月16日日记中的苦涩附言,这是该剧在坦佩雷首演的五天之后:
我离开后,米兰小剧院的哑剧老师(一个西西里女孩)爱上了阿图罗,阿图罗除了阿尔弗雷多之外,还勾搭上了一个加拿大女孩——一名学生。(阿尔弗雷多自己对女孩们感兴趣,这是他和阿图罗争吵的根源)。一个聚会,每个人都喝醉了,西西里女孩上演戏剧性的一幕,哭泣,诅咒,砸东西。似乎她在了解到阿图罗与许多男孩有关系(阿尔弗雷多是其中之一)后放弃了他,但为时已晚,因为阿图罗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加拿大女孩。
同样令人失望的是上帝达里奥的行为,在弗兰卡离开后,他有一个年轻女孩——许多年轻女孩——在他的膝盖上,在公共场合亲吻和爱抚,再次使用位置——我是说他的权力。非常糟糕的品味。他真的不太关心人,至少不关心个人。在记者面前变得彬彬有礼。然后a发现Sara(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女孩)实际上不敢告诉他在洗衣店的事情——他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Memphis”,是m的财产。所以那些为他工作的人都害怕他——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加以利用。
艺术家和艺术之间的界限永远是有争议的领域。作品的力量能抵消创作者的弱点吗?昂斯沃斯的最后一篇日记似乎是出于失望,一个像佛这样有天赋的人也能如此卑鄙地滥用权力,更不幸的是,他的职业生涯是建立在伤害那些剥夺他人自由的人的基础上的。
菲亚斯科vs达里奥佛
据我们所知,昂斯沃斯只为公众写过一次关于他在翁布里亚山坡上的夏天的文章:1985年12月为《卫报》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当天晚上第四频道(Channel 4)正在放映的一部关于佛的纪录片的预告,对这位意大利大师那个月的行为基本上是一种不痛不痛的描述。它描述了排练的混乱,但掩盖了昂斯沃斯当时记录的对佛多重缺点的看法。他在《卫报》的文章结尾写道:
在我看来,在恶魔岛的自由大学里,我目睹了一种权力和控制的行使,就像伊丽莎白所做的任何事情一样不懈。但是,在福仁慈而急躁的庇护下,在那些山坡上,一些重要的人类事务已经在那里进行了。我很高兴也很感激能看到它。
那在坦佩雷的演出呢?如果说福的导演技巧让芬兰演员感到困惑,那么舞台上的表演结果也同样让芬兰观众感到困惑。芬兰发行量最大的瑞典语报纸《Hufvudstadsbladet》刊登了这篇评论,标题醒目:Fiasko av Dario Fo——“Dario Fo的失败”。
评论家Marten Kihlman写道,尽管人们对这部剧抱有很高的期望,但观众的反应却“不温不火”:
就我而言,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看过的十部Fo戏剧中,没有一部是如此神秘而冗长的。
关于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人们写了很多(也做了很多推测):她被描述为喜怒无常、嫉妒、贪婪等等。然而,佛对这位可怜的处女女王的刻画与众不同:在第一幕中,她是一个经常尿尿的可怜的歇斯底里者;第二部则是撒切尔夫人和麦克白夫人的结合体。
佛对人类的伊丽莎白并不感兴趣——她只是代表了权力,一个方程式中的给定因素,其结果也是给定的:权力导致腐败,权力导致滥用,权力与愚蠢结合是令人憎恶的。这一切佛以前都说过,说得更专心、更尖锐。
评论家确实对布景设计师给予了一些赞扬。
虽然他严厉批评了表演(“太吵了”,“没有魅力”),但他只把责任归咎于一个方面:“不应该因为剧团经历了致命的戏剧考验而受到指责:他们遵循达里奥·福的指示。”甚至大师们有时也会失手。”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