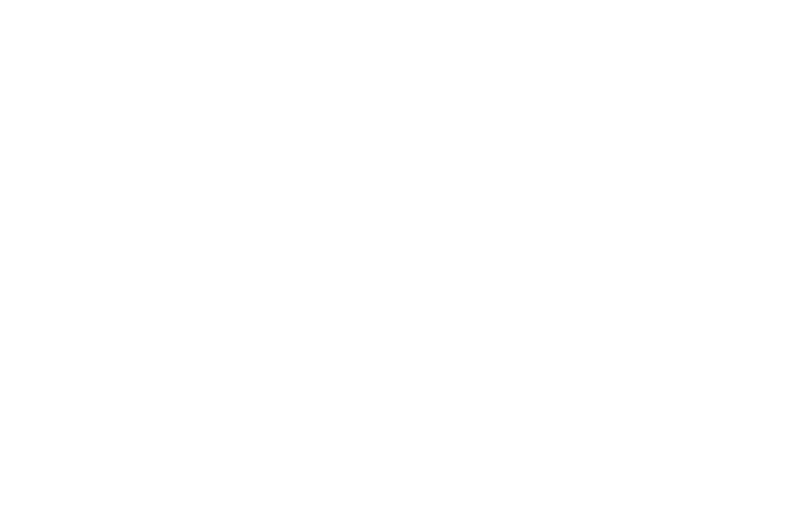她的突破已经并将继续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并为那些受这种令人心碎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影响的人带来真正的希望。由于她的杰出努力和成就,Tabrizi教授被授予本年度著名的MRC千年奖章。
伦敦大学学院皇后广场神经学研究所的Tabrizi教授回顾了她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对科学研究的热情和为患者提供治愈方法的不懈努力,她说:“我真的很喜欢医学,我对神经科学感到非常兴奋。爱丁堡的医学系相当老派,在第二年,你真的要花一年时间解剖一个人的大脑。”
Tabrizi教授第一次遇到亨廷顿舞蹈症是在她在伦敦大学学院的MRC临床培训博士学位期间,研究神经退行性变中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当时导师Tony Schapira教授(伦敦大学学院皇后广场神经学研究所)带她去养老院收集患者的皮肤活检。
她说:“当时我遇到了很多病人和家属,他们都是晚期患者。这种疾病影响年轻人的方式真的让我震惊,因为这些人都是20多岁、30多岁和40多岁的晚期疾病患者,他们仍然能够与我互动并认出我。非常感人。”
亨廷顿舞蹈症是由突变的亨廷顿蛋白在神经元中的积聚引起的。这会导致渐进性细胞死亡,表现为协调能力、不自主身体运动和精神能力的毁灭性恶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遗传的,受影响的人的孩子将有50%的风险患上这种疾病。
2009年成为正教授后,塔布里齐教授决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和寻找急需的治疗方法上。她与她的前博士导师和长期合作伙伴吉尔·贝茨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大学学院皇后广场神经学研究所的英国痴呆症研究所)一起,于2016年建立了伦敦大学学院亨廷顿舞蹈病(HD)中心。尽管对科学的好奇心使塔布里齐教授进入了这一领域,但现在是她所关心的那些人的希望推动了她的工作。
塔布里齐教授说:“从1997年我开始做诊所以来,我照顾了几代病人和家庭,遗憾的是,他们都去世了。我照顾过十几二十几岁的人。父亲、儿子、母亲因为艾滋病失去了丈夫和三个孩子。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我对找到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方法充满热情和决心。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一生的工作,我专注于它,排除了很多事情。我意识到专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作为一名临床神经科学家,这种动机促使Tabrizi教授发表了350多篇科学论文,并推动了多个开创性项目,改变了亨廷顿舞蹈病领域。这包括我们对潜在生物学的理解,我们如何预测、监测和测量疾病,何时进行最佳干预,以及如何优化临床试验。
Tabrizi教授还负责设计和运行IONIS制药公司反义寡核苷酸(ASO)疗法的开创性全球I/IIa期试验,其结果在2017年底成为头条新闻,因为首次证明了反义介导的毒性蛋白抑制在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成人中。
对于Tabrizi教授来说,合作是这一进步的核心,并对她和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

她说:“这些年来,我所有的工作都是真正的合作。我在HD中心与吉尔·贝茨教授、埃德·怀尔德教授和雷切尔·斯卡希尔博士(都是伦敦大学学院皇后广场神经学研究所的人),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皇后广场神经学研究所的许多其他人都有一个密切的社区,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一个全球网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大流行期间真的很痛苦,因为我真的错过了旅行和与每一位同事的互动。所以我非常喜欢合作,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找到治疗这些疾病的唯一方法。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Tabrizi教授重视的不仅仅是与她的同行的互动,从1994年为伦敦大学学院皇后广场神经学研究所的David Marsden教授和Anita Harding教授工作,他们分别是运动障碍和神经遗传学领域的先驱,到与DNA修复专家Gabriel Balmus博士(剑桥大学英国DRI)等研究人员建立联系,而且她还指导下一代科学家继续这项重要的工作。
在过去的16年里,她成功培养了33名博士生,其中包括17名临床医生。塔布里齐教授在一个以白人男性为主的领域取得了成功,因此平等、多样性和包容也是她最看重的事情。就像她的研究一样,她站在最前面。
塔布里齐教授解释说:“我真的热衷于鼓励多样性。我认为,当你成长为第一代移民的孩子时,你会看到你的父母所面临的困难。我还积极参与了美国医学科学院(Academy Medical Sciences)针对年轻女科学家的指导项目“Sustain”。我帮助解决了不少大问题,因为这些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设法让自己得到支持,度过难关。
塔布里齐教授热衷于向学员灌输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是他们与失败的关系。
她说:“我不知道谁没有在某些方面失败过。学习适应能力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和查尔斯·魏斯曼(Charles Weissmann)一起做我的第一个博士后时,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我发了一篇论文,里面有一些很棒的数据,我想。一位审稿人回来后写道,“如果这是20年前提交的,它会很令人兴奋”,我真的很沮丧。那时,查尔斯告诉我,为了在科学中生存,我需要长出更厚的脸皮。”
2021年3月,治疗亨廷顿舞蹈病的开创性ASO疗法的III期试验突然停止,因为治疗组的患者比安慰剂组的患者进展更糟,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失望的了。

她说:“这很难接受,几天后,我不得不向大约700名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发表演讲。我们还没有看到数据,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我真的很诚实,那不是对我自己的失望,而是对所有遭受打击的病人和家人的失望。我治疗的病人都很棒,我为他们感到很难过。他们真的非常悲伤。”
尽管遇到了挫折,Tabrizi教授仍然充满希望,并热衷于从那次失败中获得的每一点知识,以确保更好、更安全的试验。未来的试验还将受益于她的其他开创性进展,包括生物标志物安全性数据和最近开发的用于定义疾病进展的亨廷顿氏病四阶段分期系统,类似于癌症领域的革命性进展。这将有助于在临床开始前几十年进行临床试验。
这也许是亨廷顿舞蹈症最悲惨的一面,它定义了围绕它的社区的最大力量。正如塔布里齐教授解释的那样:“父母、孩子、兄弟姐妹、孙子孙女都可能受到影响……这是一种家庭疾病。对于在这一领域工作的每个人来说,有些人甚至本身就带有突变基因,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亨廷顿舞蹈症家庭的一员,而患者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通过她扮演的各种角色——研究员、导师、同事、导演、发言人、倡导者、临床医生——以及Tabrizi教授在扮演这些角色时所表现出的关心,她激励着这个家庭,并将这个家庭团结在一起。
在谈到继续专注并提供那些迫切需要的治疗时,她说:“我不会放弃。我很顽强。就像狗啃骨头一样!”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