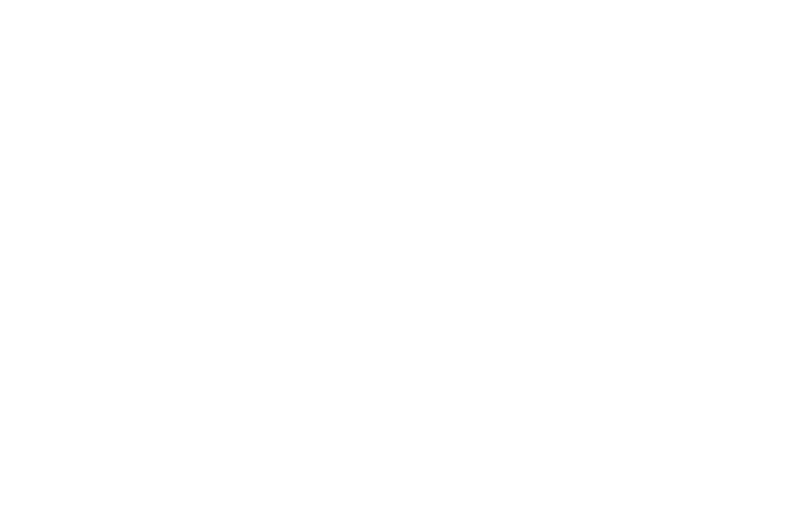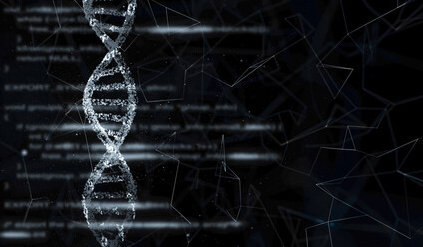这是一次去希腊的实地考察。这就是一切的开始。那是 2017 年秋天,我陪同一群耶鲁学生执行一项本质上是实况调查的任务。这次旅行是我与 Zareena Grewal 副教授共同教授的难民叙事课程的一部分。10 月中旬,我们班没有在旧校区的 Linsly-Chittenden 礼堂见面,而是登上了飞往希腊的飞机。我们班一分为二。Zareena 带领一群学生前往雅典报道一家废弃的旅馆,希腊无政府主义者与寻求庇护者并肩生活在那里。(她在大西洋上写过这个.) 我带领另一批学生前往莱斯沃斯岛,然后启程前往欧洲最臭名昭著的难民营之一莫里亚。我们的目标之一是记录那里的情况并发表我们的发现,我最终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做到了这一点。
作为一名记者,我习惯了一个人工作。无论我做出什么选择,或承担什么风险,都是我一个人的事。这次旅行是不同的:在我在希腊的整个时间里,我都担心我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失去我的一个学生。内心深处,我是一个焦虑的父亲。奇怪的是,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班实际上多了一个新成员,一个来自难民营的年轻人——一位来自摩洛哥的前数学老师——他的名字叫扎卡里亚。
从一开始,我们就都被 Zakaria 吸引住了。我们被他轻声细语的举止、慈祥的眼神和明显的智慧所折服。我也立刻被扎卡里亚的衬衫所震惊。那是一件旧的 Izod 高尔夫球衫,尽管营地条件非常肮脏,这件球衣还是崭新的。这是一个小细节,但值得注意,表明这是一个人在悄悄地反击他周围的腐烂。
我们一见到扎卡里亚,他就开始跟着我们转,好像在旁听课。同学们都喜欢他,我就让他跟着去了。当时,我没有考虑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继续之前,值得将场景设置在莱斯沃斯岛,这个故事真正开始的地方。想象一下楠塔基特岛:原始的海滩、闪闪发光的游艇、豪华的旅馆。现在设想一个拘留中心,笼罩在带刺铁丝网中,岛上内陆关押着近 6000 名囚犯——男人、女人和儿童。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想法。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访问时莱斯沃斯岛上存在的现实。
该岛通常被称为度假胜地,但从 2015 年春天开始,它作为难民中转站而声名狼藉,其中许多是叙利亚难民,他们将前往西欧。他们乘坐危险的过度拥挤的橡皮艇在大海中冒险。他们成千上万。你可能还记得那些令人痛心的照片,包括一个穿着红色衬衫和蓝色短裤的蹒跚学步的孩子被冲上岸,死了。
抵达莱斯沃斯岛的难民继续前往希腊大陆,然后向北前往马其顿——沿着陆路前往德国或更远的地方。但最终欧洲厌倦了这种涌入。许多欧盟国家向希腊施压,要求其停止流动,并有效地将莱斯沃斯岛和其他类似岛屿变成巨大的围栏。莱斯沃斯岛很快成为一个巨大的瓶颈,人类的苦难在这里被遏制和遗忘。
到我的班级访问时,即 2017 年秋天,情况已经很糟糕了。莫里亚营地大约有六千名居民,是其最佳容量的三倍。毫不夸张地说,营地人满为患。在附近的树林里,难民和移民建立了一个由无数棚屋和临时帐篷组成的“森林营地”。到达摩瑞亚后,我们先去了森林营地。那里的基础设施并不多,除了一张金属桌子,上面满是苍蝇,当局偶尔会把食物放在那里。“人们在分发食物时发生冲突,”我们的翻译解释说,他也住在营地。我们可以闻到人类排泄物的恶臭。
我们一到森林营地,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我们被误认为是救援人员,几个愤怒的人向我们搭话,要我们喝水和看医生。就在那一刻,我们遇到了扎卡里亚,他穿着伊佐德高尔夫球衫走到我们面前,自我介绍。他身上有一种让人完全放松的冷静,所以,当他邀请我们回到他的帐篷时,我暂时同意了。当我们冒险深入森林营地时,我可以看出我的一些学生正在看着我,好像在问:你确定吗?
我们边走边走,Zakaria 开始向我们介绍他自己,尽管我们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了解他的全部故事。扎卡里亚是个孤儿。他不确定自己的确切年龄,但在他长大的摩洛哥孤儿院,他们推测他出生于 1990 年。他于 2008 年离开孤儿院并继续学习农业,不过他很快就辍学了学校出于经济原因。有一段时间他当了数学家教,但他仍然很穷。扎卡里亚说,作为柏柏尔人——摩洛哥的少数民族——他面临着更多的困难。
2015 年,扎卡里亚前往土耳其,认为他可能会继续前往以色列并成为一名移民工人。当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馆拒绝给他签证时,他的计划失败了。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从地理上讲,最快的路线是前往距土耳其海岸仅 4.1 英里的莱斯沃斯岛。像许多其他移民和难民一样,他雇用走私者乘船带走他。他进行了三次尝试。第一次,他被土耳其当局抓获并遣返。第二次,他的船翻了。但第三次,他成功穿越,敢于盼望新的生活就在眼前。
“当我到达莱斯沃斯岛时,”扎卡里亚回忆道,“我以为我要实现一个梦想:去欧洲,在那里我会发现一点民主、一点稳定和一点点好-存在。” 相反,他被送到莫里亚,在那里他几乎吃不饱。混乱统治。居民们在血腥的小冲突中战斗——通常是宗派之争,阿富汗人对阿拉伯人。当局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驱散他们。
当我们终于到达 Zakaria 的帐篷时,一些杆子上盖着一块饱经风霜的帆布防水布,他非常拘谨地接待了我们,并提供了一大瓶未开封的水:在这样的地方是一种珍贵的商品。帐篷入口上方张贴着用阿拉伯文潦草写下的告示:这个帐篷不是专供一个人使用的。这是每个有需要的人的家,请你不要说脏话,不要没有礼貌地生活。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你也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示意我们进去。帐篷又黑又窄,我和学生们小心翼翼地爬进黑暗中。里面,几个男人盘腿而坐,凝视着远方。他们对我们的到来反应缓慢,就好像从某种深度的冥想状态中醒来一样。一次一个,他们自我介绍。一些人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一个是法律专业的学生,另一个是工程专业的学生。“我学的是心理学,”第三个人说。他们一起尝试分享知识——例如互相教授希腊语和英语。他们计划为营地里的孩子们创建一所学校。
但那一刻,他们心中最先想到的就是冬天。
一名男子恳求地告诉我们:“你们必须为我们找到解决办法,因为冬天来了,水会冲进我们的帐篷!”
我们的翻译补充说:“下雪时,雪会达到很高的高度。所以人死于严寒。但是这个帐篷在冬天不起作用。这里有很多人患有精神疾病,他们真的想自杀。”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我的学生记录了莫里亚的情况。我们目睹了一场骚乱、一场抗议,以及大批离开并在附近的米蒂利尼镇避难的居民。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扎卡里亚都跟着我们。
他似乎很喜欢这些学生,但我怀疑他也希望我们能以某种方式帮助他。
在莱斯沃斯岛的最后一晚,我们在一个港口小镇的一家简陋咖啡馆外出就餐,学生们邀请了 Zakaria。我们都有说有笑。我注视着扎卡里亚,他似乎陶醉于夜晚的轻浮和轻松。然后我们把他送到了森林营地。那时已是黄昏,森林的阴影浓重重叠。夜是温暖的,夏日的最后一丝曙光。当 Zakaria 从我们的货车上下来时,我们蒙上了一层阴影。回酒店的车程很长,我们很少说话。
回到耶鲁后,我们与扎卡里亚和我们认识的其他一些人保持着联系。我的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关于她所目睹的布道,在她家的教堂发表,并为莱斯沃斯岛上的当地慈善机构筹集资金。我们也试图帮助扎卡里亚。我们给他送了一个暖和的睡袋和钱。
随着冬天的临近和气温的下降,我时常想起扎卡里亚。我希望,不管怎样,他的帐篷会保持干燥和安全。但他很快传来消息说他的帐篷着火了,他失去了大部分财产。然后,不知何故,他设法离开了莱斯沃斯岛并到达了雅典。我希望最好。但后来他给我发了一条 WhatsApp 消息,说他已经回到莫里亚了。我回信说:“为什么???怎么回来了?” 他回答说,他“像条狗一样流落街头”。他补充说:“[雅典]没有房子。饿死了。我希望我死了。” 我回信劝他不要放弃。然后我发了几封疯狂的电子邮件给我在莱斯沃斯岛上的非政府组织中的联系人,包括乐施会和 HIAS,告诉他们关于 Zakaria 的事,并表达了我对他可能自杀的恐惧。我的联系人会见了他并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律师,谁同意帮助他回到雅典并在希腊寻求庇护。一段时间后,扎卡里亚给我发了一张他在开往雅典的渡轮上的照片。他附上了一条信息:“我在汽船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谢谢你,我亲爱的兄弟。. . . 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帮我的人。”
我报道难民危机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知道扎卡里亚的麻烦远未结束。他没有钱。他没有工作。他不会说希腊语。他没有庇护。而且他没有轻松或安全的方式到达西欧,这是他的最终目标。另外,我不完全确定为什么我会如此关心这个特殊的移民。我以前报道过难民。那为什么是这个人?也许是因为我的学生一直在问他,我觉得有必要消除他们的顾虑?还是我想向自己和他们证明我是一个好人?当然,我已经捐给了慈善机构。但这次不同。我一直在想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当他走出我们的面包车,穿着他的悬臂梁衬衫溜进阴影里时。这幅画让我印象深刻。
我想帮助他,但我能寄多少钱是有限制的。我需要在这个事业中招募其他人:当地人,当地人。然后,突然,我想到了耶鲁校友网络。但是希腊和其他地方的校友真的会同意帮助一些随机移民吗?
我开始向希腊的耶鲁校友发送电子邮件。我介绍了自己,并解释了我的班级如何认识扎卡里亚并与之成为朋友的故事。我保持简短。我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这些电子邮件:“我写信是因为你有机会帮助他。您或您认识的任何人能否为他提供一份工作?我和我的学生将不胜感激。”
最早回复的耶鲁音乐家之一是一位名叫 Nektarios 的音乐家,他正准备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一场音乐会。“我们会为你的朋友想出办法的,”他向我保证,并补充道:“就像安提戈涅那句古老的话那样…… . . 我们生来就是为了爱,而不是为了恨。” 他很快发送了一封后续电子邮件:“我已经联系了雅典的两位非常重要的人。. . . 我还给了他们一位与难民正式合作过的好朋友和天才翻译的电子邮件。. . . 他也可以为我们的朋友扎卡里提供便利。” 我喜欢他称他为“我们的”朋友。
不久,另一位亚烈狄奥尼修斯与扎卡里亚会面,并慷慨解囊。就连那些帮不上忙的耶鲁人也深表歉意。一位写道:“我想这正是我对您的兴趣和善意的真诚感谢,这让我感到不安。” . . 我无法为我们的好朋友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 作为一个经常报道穷人的困境和特权者的冷漠的人,我对这种悲情的流露感到惊讶。
就好像我母亲生病了,我请了这些人帮忙。
2018 年 2 月,扎卡里亚给我发短信说希腊政府拒绝了他的庇护申请。他说他将越过边境进入阿尔巴尼亚,开始前往西欧的旅程。到三月,他在黑山。我找到了一位名叫 Djordje 的耶鲁人,他愿意提供帮助,但 Djordje 在塞尔维亚——一个对难民来说很困难的地方。扎卡里亚继续努力。在克罗地亚,他和一群移民同伴在荒凉刺骨的土地上走了十五天。党内一人死亡。扎卡里亚说,他的同行者靠吃蠕虫和昆虫来生存。
最后,在四月份,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我现在在斯洛文尼亚。” 我立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在欧盟内部。他成功了,虽然他仍然“没有证件”,但他的前景有了很大改善。两天后,他从意大利发来短信。我把他和另一位耶鲁校友联系起来。扎卡里亚继续前往法国,最终前往西班牙。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以斯帖的年轻女子。一天晚上他在一家酒吧外出,他们开始跳舞。她的母语是加泰罗尼亚语,因此他们依靠谷歌翻译来相互理解。但即便如此,Zakaria 说,他们还是有联系的。以斯帖在一个日托项目中与孩子们一起工作,并且是一位有抱负的作家。他们开始同居。他们结婚时,我送他衣服,这样他就有好衣服穿了。他告诉我他的尺码是 28。就像一个专横的亲戚,我发现自己希望他不要那么瘦。
在很多方面,我仍然几乎不了解这个人。我仍然质疑自己帮助他的动机。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耶鲁同学也帮助了他。我怀疑这是因为我们以某种方式在大脑中对他进行了重新分类。我们已经把他从“其他”类别中移出——生活在桥下和森林营地中被遗忘的人类的诅咒领域,那些我们避开视线的人。Zakaria 凭借他善良的眼神、干净的衬衫和坚持不懈的文字,逃离了那个领域。出于诡计或运气,他曾短暂地加入了我的班级——延伸为耶鲁——无论这个想法多么荒谬,无论这种联系多么微弱,这都很重要。我仍然觉得这令人困惑。而且,老实说,有时我对这个男人如此依赖我感到不满。
去年春天,我和妈妈一起去西班牙旅行了一个计划已久的假期。我们在巴塞罗那停留,我安排与扎卡里亚会面。当他出现在我的旅馆时,他看起来很好:微笑着,晒黑了,英俊。我们坐下来喝杯茶,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生活。他有一个两岁的女儿。埃丝特写了一部浪漫小说,正在写一个关于扎卡里亚生平的故事。但她的家人并不高兴她嫁给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实际上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她因为我失去了家人,”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
喝完茶后,扎卡里亚提出要带我和妈妈游览这座城市。他是一名三轮车司机,兜售一辆后座敞开的三轮自行车。我们继续前进,Zakaria 带我们游览了这座城市。这是一个完美的春天。阳光透过这座城市雄伟的橡树树冠,洒下斑驳的光芒,洒在安东尼奥·高迪 (Antonio Gaudi) 的建筑上。当我们航行时,Zakaria 转过身来,脸上闪过一个微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让自己沉浸在天真而永恒的希望中,希望事情有时能有好结果。
注:本文由院校官方新闻直译,仅供参考,不代表指南者留学态度观点。